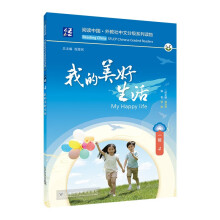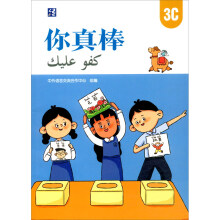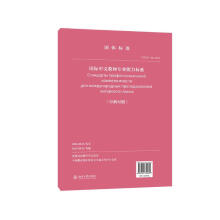一 语言和思维与文化
语言是形象的象征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语言的形成和使用与人类大脑的结构有着直接的关联。从人脑的物理构成来看,两个半脑分工不同,左半脑负责语言,其功能为语言思维;右半脑负责形象,其功能为形象思维。从语言形式来看,中西方语言形式
的不同直接造成了两种语境下人们思维方式的不同,首先体现在文字书写方式上。中文文字的音、形、意的结合使得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英语这种字母文字割裂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表现为纯粹记录语言的符号,形成了西方人较强的语言思维。
研究表明,语言和思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诸多西方学者也不同程度地表述了这一思想,黑格尔在《逻辑学》第二版的序言中对逻辑的对象——思维形式进行了讨论,认为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的语言里。中国学者强调语言与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认
为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易经 · 系辞》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可见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有限性。庄子说“得意而忘言”,就是将意义从言辞的局限中释放出来。《庄子 · 秋水》记载,“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老子《道德经》开篇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都是这种思想的不同形式的呈现。
语言和思维的内容根基于文化语境之中,是相关文化思想的具体表现。鉴于中西方文化迥然相异,语言形式和思维内涵也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内容。从翻译的视角看,翻译的对象是具体的语言,但翻译的实质是语言背后的文化及该文化所体现的思维内涵。本质上讲,译者处理的并非文字,而是文化。文化元素如何在译文当中得到恰如其分的呈现,是
译者和翻译研究者应该尤为关注的问题。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