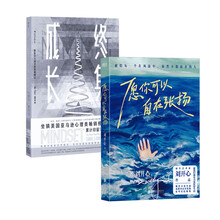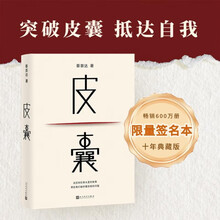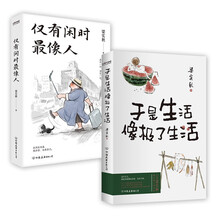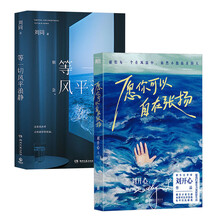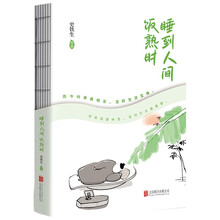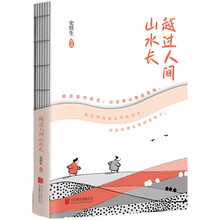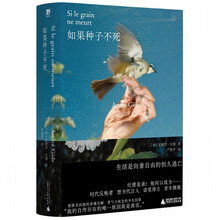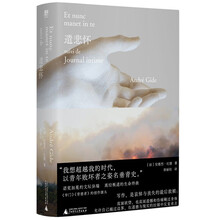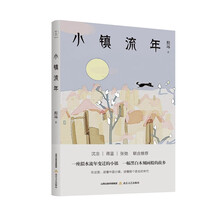我最思念的那一匹马
亲爱的孩子: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天下父亲,都是子女厚实的依靠,都是子女宽阔的大道。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父爱不是那么细腻,却是这般稳重,它不是甜蜜的唠叨,却句句语重心长。父爱的珍贵,在于它凝聚了人生的经验,在于它充满了人生的智慧,在于它能让子女的人生顺畅、生活甜美。
那些缺失了父爱的人,更懂得父爱的价值。那些经历了坎坷的人.更知道父爱的意义。那些走过弯路的人,思念中的父亲形象更无比伟岸: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那一匹马。
他是1930年的一匹马,正值英年而早逝。
那是1976年,一个历史永远不会忘却的年头。那年我12岁,妹妹10岁。那年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25万人死亡。那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相继去世,尤其是毛泽东主席的逝世,让全国人民从内心深处担忧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同天塌了一样。那年我家的天真的塌了,那年我的那匹马也去世了,他死于贫穷,他死于饥饿,他死于缺医少药。
秋风吹起时,他已经病重了,咬着牙,忍着痛,他把秋天应该干的农活全部漂亮地干完了。也许是因为有热爱社会主义的觉悟,但我更相信他是为了那点可以养冢糊口的工分。
他卧病在床不起了,大约有三个月之久。半饥饿是那个时代的常态,种田的农民吃不饱肚子是那个时代的标志之一。青黄不接的时候,饥饿处于顶峰,前心和后背总是紧紧地贴在一起。初秋时分,收了什么吃什么,变着各种花样地吃,也吃得直叫人倒胃口。比如刨了土豆的时候一日三餐都是土豆,蒸土豆,煮土豆,烤土豆,炒囫囵小土豆,炒土豆条、土豆块、土豆片、土豆泥……土豆至少有十几种吃法,好多种吃法都成了今日大酒店里的名菜,今日的这些名菜,那时候吃起来就只有一个感觉叫倒胃口。他卧病在床也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改善伙食和增加抵抗力的食物,吃的喝的东西都和健康人一个样,所不同的是他倒胃口的感觉更加厉害,很少能吃下去几口。卧床三个月中,他没有住过医院,没有请过正规的医生,没有打过针,没有输过液,也没有吃过几粒西药片儿,只煎过几副中药,是村里的赤脚医生给开的药方,大多数药材是妈妈自己到大山里挖来的。
他死了,死在数九寒天的冬月廿六日上午九点多,死时皮包骨头。他死得那么悲惨,死得那么可怜,死得那么卑微。他死前半小时,嘴里嘟嘟囔囔说个不停,就是向儿子索要一口砂锅,直到砂锅放进了被窝他才稍稍放心了一点。那匹马,他的父亲那年68岁,哀号着把自己的寿材给他使用,无奈那匹马是一匹高头大马,一米八五的个头,比他的父亲高出了十几厘米。一副用了几十年的大门门板改造成了他的棺材,坟工们抬着去墓地,一路发出吱吱扭扭的响声,走到半路就快散架了。善良的村民、负责的坟工们格外小心地保护着棺材,才勉强得以正常人葬。
他的死,让我失去了父爱,成了我心中一辈子的痛。
我常常想,其实我还是应该恨他的。他不该对子女那么疼爱,不该疼爱得那么细致入微,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孩子带在身边,孩子们无论怎样闹腾和顽皮,他都总是以微笑对待。他不该不舍得让子女吃苦受罪,自己饿着肚子把烤熟的嫩玉米全部给子女吃,去外婆家的时候总是一根扁担两个框子,前头挑着女儿后头挑着儿子,一挑就是10多里山路。他不应该每天晚上睡觉前都给子女讲故事,讲那些已经被多少代人讲来讲去的老故事,声情并茂,情节引人,束缚了子女的思想,以至于他们从小就只知道循规蹈矩,没有享受过“胡作非为”的“快乐”。他不应该总是微笑着说事情,从不打骂子女,以至于子女成年后也不会打骂自己的子女。他不该在那样一个不重视读书的年代里决心要供给子女读完高中。他不应该在临终时告诉妈妈家里还欠着村民金鱼六元钱,六元呢,在当时那是一个乡镇干部一个星期的工资!以至于妈妈把这个钱还上以后村里的人在好多方面都对我们照料有加。他有太多太多的不应该,怎么能让人不恨他?
据说,他也有一些让人敬佩的地方,只是和我关系不大,并且都是听村里的街坊邻居们讲的,几十年前他们就这么讲,几十年后他们还这么讲,村里的什么都在变,唯有村民们讲述的这些故事没有变。
那一匹马,他果真有那么优秀吗?故事的真实性不得不让人怀疑。
村民们说他勤劳勇敢,积极进取,是种田能手,传统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犁地、播种、锄草、间苗、固根、培土等他都是村中一顶一的好手。村民们说他心灵手巧,村里所有的手工业作坊都离不开他,榨油坊、砖瓦场、编框场都离不开他。村民都说他心地善良,邻里乡亲有事,他总是主动帮忙,帮助村民垒火熠、盘热炕如同给自己家干活,不嫌脏不嫌累,不辞辛劳。村民们说他一身正气,路见不平总要伸张正义。村民们说他在柳沟铁厂炼铁、在分水岭修路、在关河建设水库都是劳动模范,只要开表彰大会总有他的奖状。村民们说他对妻子特别负责,妻子因故成疯,他能如影随形三年而使妻子得痊愈。村民们说他对继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