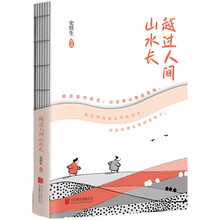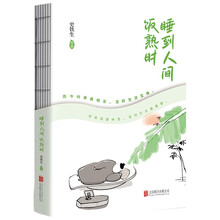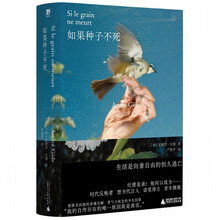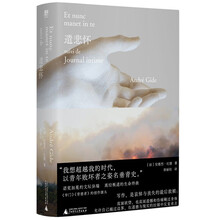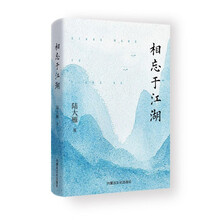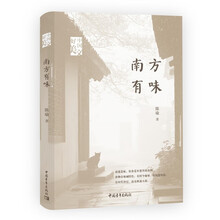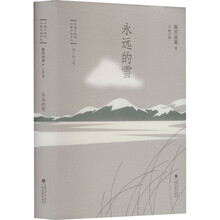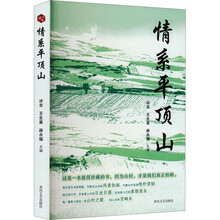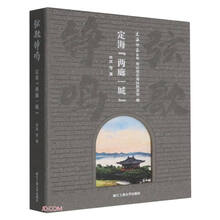《云阶月地(摄影散文)》:
院里
那是个与山寺结缘的小山村,地处闽中永泰县西北部,它有个美丽的名字叫院里。村庄群山环抱,巍峨的高盖山犹如宝盖浮空,紫云覆盖,山问翠竹隐隐,四季常青。密布四周的沟涧,在村中央汇成小溪,小溪的流向,便是山村通往外面世界的豁口。
恰似农家小院名字的小村落,因山上千年古寺香火萦绕,让人闻到了一股吹拂着久远而又古朴的味道。至于这个村落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多,但外婆与母亲的悲欢离合却曾在这里上演,因此,我对它有了特殊的情结。
外婆从邻村嫁到院里,在那风雨飘摇的年代,出嫁不过是乡下女人命运的一次简单迁徙。至于夫家殷实也好清贫也罢,不是她的关注能追求得到,只要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便可心安,且无怨无悔。可外婆的境遇自从她嫁到林家之日起,如同高盖山上佛徒参禅、道众修仙、儒生研读那样充满了艰辛与悲欢。
有人说人生是一出戏,一旦粉墨登场,后戏如何演绎就很难把控了。1930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外公经营的店铺大门被一群士兵野蛮地敲打着,熟睡的他被一阵急促的声音惊醒。他睡眼惺忪,刚打开一条门缝,一只乌黑的枪眼就对准了他的脑门。
外公侠肝义胆,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经商所在的德化县城。那时共产党队伍不断壮大,在进步人士的引领下,他积极参与地下党活动,不断拿出经商所得资助地下党开展工作。店铺开在国民党团部附近,平时士兵与军官常出入,团长老婆便是店里的常客。有一天,外公正与地下党接头,突被这位女人撞见,战场失利的团长,把心中怒火喷向了外公。急欲撤退的团长恼羞成怒,居然扣动了扳机,一声闷响结束了外公年仅29岁的生命。那年母亲3岁舅舅7岁。
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的外婆从此失去了生活依靠,柔弱的双肩也因此挑起了抚养两个孩子的重担。在男耕女织的年代,靠她养育两个孩子的艰难,让她失去了信心,心力交瘁的外婆不久便改嫁他乡了。
对于外婆,我始终没有印象,但在童年朦胧的记忆里,那次母亲肝肠寸断的情景,后来,我便推定是外婆过世赴丧的悲切。
外婆改嫁到邻村的蔡氏人家,再生育一男一女。尽管母亲与后来的弟妹感情亲密无间,可她认定的娘家,嘴上不说,心里装的依然是她的出生地——院里。
逢年过节,或是寒暑假,母亲都会带我回院里。爬上一座山,沿着崎岖的山路,绕过几道梁,上下几弯山垄就到了。母亲苦涩的童年,我都是在跟着她后面,循着她的脚印踏步前行中,一次次听取并反复问询后烙进记忆的。
外婆改嫁后,母亲与长她4岁的哥哥相依为命,收养她的阿婆的刻薄,让她记了一辈子,这段故事我听得最多,懂得也最多。
时光荏苒,舅舅初中毕业了,一表人才的他,学业优秀并写得一手好字,十里八乡的人都称他是秀才。熬过艰难,苦尽甘来的兄妹俩,逐渐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善良的人们为他们苦尽甘来而庆幸,指待着天日朗朗,未来灿灿。
天有不测风云,处在抗日与国共交战的动荡年代,藏在深山的壮丁,同样无一幸免,被国民党军队瞄上,刚满18岁的舅舅,就这样被抓走,送上了炮火连天的前线。舅舅被抓去当兵的情形,深深烙刻在母亲的记忆里,每一次当我们兄弟姐妹聚集时,或因某件相关的事情,母亲都会挑起话题,给我们讲述她和舅舅的过去、舅舅被抓的经过,憧憬着舅舅如果不被抓丁可能会有的光明前景,以及她一生对舅舅的牵挂。
我上高中的时候,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开始解冻,国民党老兵不断回乡寻亲。有文化的堂哥告诉母亲,在台湾电台里听到过母亲常念叨的舅舅名字。一石激起千层浪,母亲魂牵梦萦的哥哥,在她脑海里顿时被激活,泯灭的希望重新点燃,只要听说有人从台湾回来,她一定不辞辛苦登门问询。为了找到舅舅,她还让我写了一封寻人启事,寄往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有人听到电台播出我们寻找舅舅的启事,但始终未得到回应。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脑海里不断闪现着许多假设,每个假设都成为她一生无解的方程,冥思着、苦想着。
母亲有两个娘家,一个是出生地院里,另一个就是外婆后来改嫁的尤墘。这两个地方在母亲的心里都是娘家,可在我记忆里,母亲回娘家,一定是先到院里,再去尤墘。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