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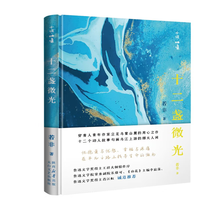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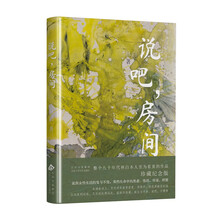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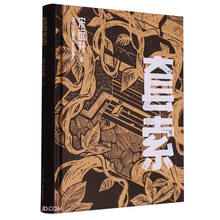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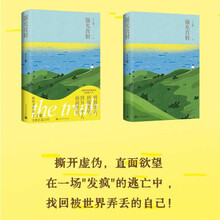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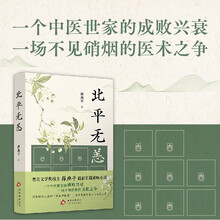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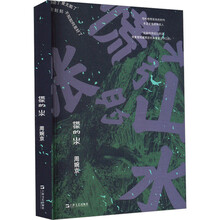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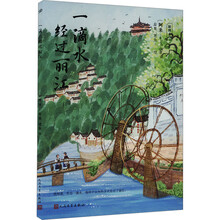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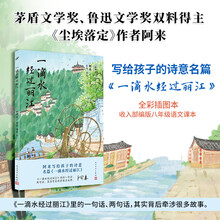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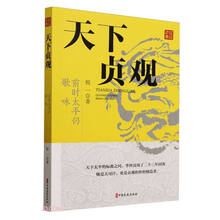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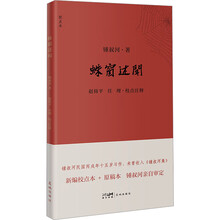
长街如河,人生如浪,一部生动鲜活的上海民间史
一条被填埋的河,化成蜿蜒的长街;一片交织的市井,藏着半部上海史。从填浜筑路到街巷纵横,从解放初到改革开放,盈虚街的变迁是上海城市化的缩影。从吴淞江到肇家浜,1958年的填浜筑路,让“盈虚浜”成了时代的隐喻——河水流逝,街道兴起,洋房、石库门、棚户区在此角力,织就一张市井浮世绘。
一座街坊,两个家族,三代纠葛,四世同堂
“盈虚街没有秘密,只有人心在明暗处涨潮退潮。”吴姨娘带着女儿“小茧子”,从小山村踉跄踏入这座迷宫般的街巷。她们仰望着长街尽头最豪华的花园洋房,如同仰望一座遥不可及的命运灯塔。但在这条街上,没有绝对的赢家与输家:石库门里的旗袍太太,光鲜下藏着旧时代的伤疤;棚户区的小学徒,用一把铜锁撬动人生的转机;弄堂口的“老克勒”,半生守着褪色的钢琴和尊严……王小鹰以工笔细描弄堂烟火,写透邻里亲疏、爱恨纠葛,每一扇门后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小人生”。
上海里弄生活的全景式、史诗级呈现
如果你喜欢《繁花》《长恨歌》,痴迷于考古老上海风情,就一定会喜欢《长街行》。书中对旗袍裁剪、煤球炉子、老虎窗光影的描摹,让旧上海的风物跃然纸上,字字生香。“洗菜的剁肉的刷锅的淘米的,手中文武不乱”“有阳光的地方,底楼人家拉出了麻绳,把一家人的被子褥子统统拿出来晒着”,这样细致入微的场景描写,好像以文字复活了整条街的灵魂。
盈虚浜,原本是一条贯通吴淞江和肇家浜的枢纽水道,1958年填浜筑路后,盈虚浜成了一条长长的街,洋房、石库门、棚户区纵横交错,各方邻舍共同构建起新的盈虚“坊”。做生活的吴姨娘带着女儿“小茧子”从小山村来到大上海,仰望着长街上最豪华的两栋花园洋房,纷繁杂沓却生机蓬勃的故事就此展开,随之而来的命运遭际和弄堂街巷人际关系的悲喜剧也拉开帷幕……
引章 赴约
深巷浅弄斜晖静,闲门繁户梧桐疏。
早春时节的黄昏,暮霭是从弄堂水泥板地的缝罅里,从石库门台阶边的苔藓里,从青砖围墙上隔年蔷薇花的茎蔓里,丝丝缕缕地升起来的,像兑了些水墨的花青石绿。晚风如羊毫,横一抹竖一抹,暮霭便渐次晕染开去,一分一寸地罩没了一幢楼,又罩没了一幢楼。
这一片屋脊很不规则,不像人家里弄房子的划一规整,也不像人家花园别墅的精致典雅。这里却是忽高忽低畸轻畸重,横生枝蔓,错落芜杂。当浓浓的暮霭罩没了这一片不规则的屋脊,它们倒变得沉静幽深起来。
这一片屋脊中的某一处,一扇稍稍突起的老虎窗口,北向的窗户咣地被推开了,急急地探出一张十六七岁光景女孩子的面孔,苍白细巧,腊梅花似的一瓣。她先是将花瓣儿朝向西北,那里半轮金红的夕阳正停在锯齿般的屋脊上,像刚刚摘下枝的鲜橙子,十分诱人。那一片灰脱脱陈年旧瓦被涂上鲜艳的色彩,像刚从高炉里倾泻出的铁水,像熊熊燃烧的火焰,是何等辉煌的景象呐!可这个女孩子却被灼痛似的眯起眼睛,失望地蹙起她远山般的淡眉,咕哝道:“怎么太阳还不下山呀!”原来,她是在等待“月上柳梢”的那一刻,这亘古不变的少女情怀哟。她还是心怀侥幸,转动玉笋儿似的颈项,将花瓣儿脸朝向东南,云遮雾漫的目光在天际寻寻觅觅,期望月牙儿能像七仙女那样不守天规,抢先登场。
东南向弄堂底处,有一片扇形的角落尚未被暮霭罩没,最后的几幢房子依然笼罩在黄澄澄的余晖中。女孩子的目光定住了——山墙亮得晃眼,爬山虎残余的枯蔓断藤纤毫毕现,那萧条凄凉的图案就像她记忆中总也抹不去的惨烈的一幕。
从前,到了夏天,那半墙爬山虎会挂满碧玉般的绿叶,密密匝匝、重重叠叠,稍有风动,便撼天动地地簌簌作响。厚厚的叶阵隔断了暑气,房间里总是阴凉,甚至都不用开电风扇。替她家做钟点工的吴阿姨常会挽只竹篮,端把竹凳,跟母亲打声招呼,便将凳子往墙脚一靠,人立上去,刷啦啦刷啦啦,一把一把捋爬山虎的叶子。爬山虎的叶子有一种带苦涩的清香。吴阿姨说,拿它熬汤喝,拔力气,还清热解毒,大伏天不会长痱子。每当吴阿姨站在竹凳上捋山墙上爬山虎叶子的时候,左邻右舍的孩子们都会聚拢来,帮吴阿姨捡散落在地上的爬山虎叶。女孩子们总是乖乖地捧起叶子放进吴阿姨的篮子里,男孩子却趁机恶作剧,抓一把叶子塞进小姑娘的衣领里,引得女孩子喳喳直叫,一边抖动衣襟让叶子落下来,一边红着脸蛋骂:“下流坯!”男孩子反倒得意地笑,故意笑得龇牙咧嘴,恶形恶状。不过,一旦有谁试图往她的后颈脖塞叶子,他便会挺身而出保护她。他的个头在同龄人中独高,男孩子们都有点畏惧他,因而她总能幸免遭遇袭击。男孩子们心有不甘,跑得远开点,一起喊:“长脚鹭鸶敲洋丁,敲来敲去敲不进……”待他做出要追的姿势,他们便一哄而散。
与那半壁爬山虎呈犄角之势的南墙上,离地一丈余,有弧状优美的半圆形阳台,那锈红铸铁围杆被余晖镀上了一层金箔,皇冠一般。围栏间参差披拂着翠绿墨绿鹅黄绿的兰叶,袅袅娜娜、摇曳生姿,阳台里总是积淀着薄薄的馨香。
女孩子的目光颤抖了一下,她看见一个温婉秀雅的女人,穿着豆青的绸衬衣,外面罩一件湖绿色网眼开司米对襟衫,正往一只只青花瓷盆或紫砂盆里植兰草。松土、剪叶、洒水,在兰叶中穿梭的身影也是一株兰。女孩子半截身子都探到老虎窗外边,她好想一头扑进种兰草女人的怀抱里。可是,那女人却转身推开垂着素花窗帘的落地玻璃门走进去了。
落地玻璃门里面是一间宛若母亲怀抱般温暖的卧室,墙壁里麦黄色的,家什是乳白蜜黄相拼的,钢琴上铺着本白挑花带荷叶边的麻纱罩,落地灯宽大的灯罩也是本白挑花带荷叶边的。笃底并排两张铜架小床,小床的素花被褥里躺着两个花骨朵般鲜嫩的女孩子。那兰草般的女人站在两张铜架小床中间,左看看,右看看,上看看,下看看,便柔柔地弯了腰肢去吻那两个女孩子光滑如玉的额头。然后,她直起腰身,径直从垂着素花窗帘的落地玻璃门走了出去,站在半圆的凝固着馨香的阳台上。她一株兰似的伫立了好一会儿,突然,决绝地踏上青花瓷盆(她并不是存心将盆中的兰草踩倒的),另一只脚便跨过了锈红的铸铁围栏。她就像瓷盆里被她踩倒而折断的一片兰叶,徘徊着盘旋着飘落下去了。
女孩子无声地呻吟了一下,并用双手蒙住了眼睛。其实,这场景并非她亲眼所见,是她怀着伤痛一遍遍地构想出来的。当时,那两张铜架床上的女孩子都睡得很熟,待她们的姨妈把她们叫醒时,她们母亲的尸体已经被人搬走了。她们趴在阳台围栏上往下看,只看见底楼通花园的石阶上有模糊的血印,血印的形状很像几片交错穿插的兰叶。过了几天,两个女孩子中稍年长的那个在阳台的兰叶中踟躅,就在铸铁围栏的一根角枝上捡到了一片窄窄的豆青色的绸布条,它夹在兰叶中间,很难被人发现。稍大的女孩子却一眼认出这是她母亲衬衣的料子,她想一定是母亲飘落的时候被铁栏勾住了衣襟,母亲的衬衣穿了好多年,丝绸料子已洗得发脆,自然经受不住一个人的分量。倘若母亲穿一件料作坚固些的衣服,肯定不会落下去了。这女孩子没有将捡到的那块豆青色如蓑草般的残绸交给她父亲,她将它捋得平展展的,夹在自己最喜欢的《勃朗宁夫人十四行爱情诗集》里。她在这诗集外面包了一层黄牛皮纸,并且在封面上用仿宋体写上“毛主席诗词”的字样。
女孩子缓缓地从手掌中抬起脸来,迷惘地望着余晖残余处——哪里还有满墙碧玉般的爬山虎绿叶?运动初始,造反派要在山墙上贴大字报,将满墙爬山虎都扯完了。哪里还有兰草葱茏馥郁的半圆形阳台?阳台早被后来入住的人用油毛毡封死,外面凌乱地搭着晾衣竿,悬着长长短短的内衣外裤、女人的胸罩、婴儿的尿布。哪里还有她曾经的乐园、那幢被人称作“恒墅”的小洋楼?年复一年,她们的楼房已经被陆续扩建的各式简易房屋包围吞食淹没了!
就在女孩子的母亲跳楼自杀后不久,她们一家就被迫搬出了恒墅,搬进现在的三层阁里。虽然距恒墅不远,却已经天地两重世界了。三层阁居中处丈余见方,一人多高,四面斜坡,至墙脚处仅能匍匐。家里用熟了的老家具几乎都不能带过来,许多东西被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奢侈品,并由一群手臂上箍着红袖章的革命群众搬了去,掼进一辆卡车,不知运往何处去了。这其中包括女孩子的聂耳牌钢琴、她妹妹的檀香木古筝、母亲的黄花梨木梳妆台,还有父亲常靠着抽雪茄、看报纸的米色羊皮长沙发。留给她们最贵重的物件就是父亲母亲的大衣橱,也是黄花梨木的,沉得像座山。父亲向革命群众恳请了半天,言明女儿都大了,父女同宿一间不方便,需要用这架衣橱做隔断,方才被允许了。这架橱就横亘在阁楼中央屋顶最高处,将房间分割成两个斜顶的小间。左边朝北的小间有一个二尺见方的老虎窗,便比较明亮,成了姐妹俩的绣阁;而后半间终日黑暗且不通风,是父亲的卧室,很难想象曾是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父亲如何在里面起居?
女孩子略略凹陷的眼窝里已蓄起两汪晶莹的泪,她咬住薄唇,强忍着没让它们滚下来。夕晖笼着的扇形愈来愈窄,只剩下水果刀似的一条了。女孩子慌忙将目光调开,重又投向西北面。就那么一瞥间,夕阳咕咚沉到屋脊下面去了,天边只余下几缕发白了的余晖,像褪了色的旧丝巾软软地耷拉着。弄堂里,花青石绿的暮霭中隐隐显现出人影活动,皮影戏似的,叽叽咕咕的日常絮语就像深潭水面泛起的渣滓。
天才稍稍转暖,仍处于“乍暖还寒”时节,上海人家屋子大都逼仄,便有人早早地在弄堂里做市面了。折叠椅、小方桌往后门口一搭,一家人吃晚饭,老对手摆开棋局,男孩子飞香烟牌子打弹子,女孩子跳橡皮筋造房子。可这个女孩子是从来不参加弄堂里的游戏的,她是个心里爱藏事的女孩子。她忘不了父亲单位里的造反派来抄家时,相邻几条弄堂的小孩子都拥到恒墅里来看西洋镜;她也忘不了那段时间常有人朝她们半圆形的阳台丢石块,有一次还把垂着素花帘子的落地玻璃门都打碎了。这些事情此刻在女孩子心里只是淡淡的痕迹,像冬眠的蛇一般纹丝不动。因为此刻她最焦急的问题是西边的太阳落山了,东边的月亮会升起吗?
女孩子再次把殷殷的目光投向东南,也是在那一瞥间,残余的日晖退尽了,沉沉暮霭笼罩了一切。层层叠叠不规则几何图形的屋脊剪影衬在紫灰的天幕上,是一出曲折离奇悲欢离合的大戏。心细如发的女孩子就在这繁复的图案中发现了一眉恬淡的月牙,嵌在犬牙交错的屋脊线中,仿佛一叶扁舟,是“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也像是那悲欢离合的戏文差强人意的结局。女孩子双手一合,惊喜地啊了一声。自下午放学回家,她就一直在等这枚月牙儿出现了!
温馨提示:请使用罗湖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长街行》,以小街景,见大上海。上海都市大变迁的一个见证。
——孙颙
一部充满世俗风情,又不失典雅的人间史诗。
——赵丽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