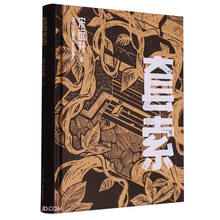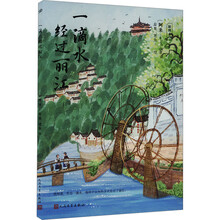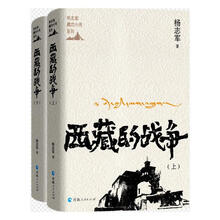《我的科尔沁》:
成长的道路很漫长,其中有个懵懂童年是我珍贵的回忆。
那年我六岁。那时候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去姥姥家跟几个表哥疯玩儿几天罢了。我的两个舅母不和,我时常在他们两家穿梭,舅母就互相打听另一个在家里净说些什么,六岁小孩儿哪有什么心眼儿,就把听到的统统告知了她们。有一天,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我成了这场战争的导火线。我母亲知道以后说:“这孩子口无遮拦,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都分不清,该打!”先脱去我的裤子,再脱去自己棉鞋,用鞋掌给我烙饼子,记得那是火辣的味道。
八岁那年冬天。母亲大人对我交代煮猪食。这个活儿真不好干,湿柴火不易燃,一个劲儿地冒青烟,两眼被熏得通红。不一会儿就得加点水,要不然猪食就煳巴了。好无聊啊,也不能离开那里,不断地添加柴火。好不容易冒热气,快要开了,妈妈揭开锅盖看了一眼说:“水太少,一会儿就干锅了,不煮烂,猪吃了不好。”说完就加进去半桶冰水。联想到我还要在那里接着坐一小时,我就委屈得不行了,坐在那里哭,不断地发牢骚。终于惹得母亲不高兴,又说了我两句,我继续辩解、理论,直到母亲生气。她拿了一根树条指着我讲道理,我却趁她不注意,一把夺了那根树条,这下事情闹大了。母亲生气地说:“让你干点家务活就这么难!你敢这样顶撞母亲!你夺树条是不是要打我了?”我知道自己理亏,但又觉得委屈,大声嚷嚷着,好让父亲听见。以往每次妈妈要打我的时候,父亲总是成为我的保护伞,把我藏在自己后边,劝说母亲,让我认错了事。可是这次父亲不知怎么的了,一言不发,坐在那里看书,任我母亲用树条翻来覆去地修理我也不发一言。恐惧、疼痛、怨恨、号叫,别人肯定以为我家在杀猪呢。我不恨母亲,却对父亲失望至极。原来原则问题上他们俩还是一致的,我要是过了那个底线,就谈不上保护与宠爱。我恨透了父亲,怨他隔岸观火,按兵不动。心想:下次你的腰疼了可别找我踩背,你打死我,我也不给你踩了,沏茶倒水都免谈,谁让你关键时刻保持沉默?
父亲是我们嘎查完小的校长。嘎查完小后来发展成为兴安学校,有了初中班级。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都来我们村上课。嘎查书记是我舅舅,精明干练的一个人。两家相互依托,相依为命,极其困难地度过了那个年代。我家里的很多农活儿都是舅舅照顾帮忙,我从他身上学了不少东西。那时候种地全靠手工,施肥、犁地、拔草、锄地、割地等庄稼活儿都学得很地道。舅舅要求很严,谁要是干活糊弄.他就声色俱厉地批评指正。父亲和舅舅的关系很铁。有一次父亲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酒壶,让我给舅舅送去。舅舅看了,莞尔一笑,就跟着我来到我们家里,他们俩乐呵呵地开始喝酒,开始谋划村里的和学校的一些事情。他俩就这样默契。
念初二的那年,父亲换了工作,调到苏木政府任司法所所长。我们家也搬到苏木政府所在地(后来舅舅家的五个孩子先后都住在我们家念初中)。初二下学期开学不久是清明。那时候大哥在苏木政府武装部上班,他骑了一辆红色125摩托车,我坐在后边,牛哄哄地出发了。那时候摩托车就是现在的宝马。春天的风很大,大哥戴着墨镜,也给我准备了一个。那时候正是墨镜、喇叭裤、燕舞牌录音机最时兴的年代。我都把自己想象成上海滩老大许文强一样的角色。村东马鞍山是我们村安放逝者的坟地,是个三面环山的风水宝地,漫山遍野的杏树,到季节,杏花开的时候那真是美极了。
我们到的时候村里很多家族上坟已经快结束了。舅舅正赶着马车拉土,看见我们,脸上毫无表情,手里拿着三套马车大鞭子,很像传说中的将军。他是有名的甩鞭手,我曾经看到过他与人打赌,站在离沙果树一丈开外的地方,人家说打哪个叶子他就能一鞭子甩过去恰好打掉那片叶子,从不失手。大哥勤快,放了摩托就抓起铁锹开始干活儿了。也许他反应比我敏锐,已经看出气氛有点不对。我反应慢,站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双手插在裤兜里,还没有把墨镜摘下来。就那么站了也就不到一分钟后,我匆忙把墨镜摘下,想拿上一个工具干点活儿,往前走两步,离舅舅稍稍近了一点儿,舅舅的鞭子火蛇一般突然眷顾我,打得我措手不及,浑身打了一个寒战。电视剧《神医喜来乐》里演的,有个皮肤病叫龙缠腰,当时我要是脱掉衣服,皮肤上的形状肯定与那个一样。全村的老少爷们儿都在瞅着呢,我都不知道舅舅为啥给我这一鞭子。小时候一起摸爬滚打的小伙子们看着我那熊样不知怎么想的,我喜欢过的那个女孩子的弟弟正好看着我呢。大哥假装没看到,干得那么起劲儿。每当看到清朝电视剧,要早朝了,一个太监,拿出鞭子,“咣咣咣”甩出几鞭子,群臣开始步入午门。我特别讨厌甩鞭子的声音。最近看了一个微信,是新加坡执行鞭刑的视频,被打者是酒驾的人。几鞭子下去皮开肉绽的,惨不忍睹。那么文明的国家,还留着这么野蛮的刑法,真是莫名其妙。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