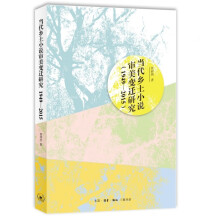《翻译、传播与接受:克罗齐美学在中国(1919-1949)》:
无论是滕固的内经验,还是邓以蛰的“境遇论”、抑或是林语堂的性灵表现,虽然他们在言说这些话语概念时借鉴了克罗齐的直觉和表现,但是有一点根本的不同的是,克罗齐美学中的精神直觉已然演变成了与现实人生及自然世界连接的生命体验。
其次,克罗齐否认物质传达为艺术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几乎所有克罗齐美学的中国接受者都发表了相反的意见,这当然受制于接受者们所处中国文化的现行结构,即他们并未真正理解克罗齐美学的逻各斯主义前提。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逻各斯”(Logos),最早用来指万物生灭变化的一定尺度,逻各斯后来成为希腊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含义为规律或理性,也有言说之意。逻各斯的基本含义是“所言之事”,因此逻各斯中心论又意味着语音中心论。在西方哲学中,逻各斯中心论是理性主义的代名词,它执着于探寻事物背后的统一本质和规律,这一本质和规律又经由言语这种活的声音直接传达。文字仅仅是传播的媒介,而且,文字的传播因为人的不在场而与本源相分离。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都认为“借助于一种文字,既不能以语言替自己辩护,又不能很正确地教人知道真理。”①文字不过是传播真理的工具,而语音则因为和思想直接接触,从而保证了意义的在场。柏拉图认为,在灵魂与自身的无言对话中,人能直觉而纯粹地接近真理。西方逻各斯中心论影响着柏拉图之后的哲学家。伽达默尔曾说:“语词的‘真理性’当然并不在于它的正确性,也不在于它正确地适用于事物。相反,语词的这种真理性存在于语词的完全的精神性之中,也即存在于词义在声音的显现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切语词都是‘真的’,也就是说,它的存在就在于它的意义,而描摹则只是或多或少地相像,并因而就事物的外观作衡量——只是或多或少地正确。”②克罗齐美学当然也没有脱离这一思想传统,他否定了传达对于艺术的意义,将艺术锁定在纯精神的领域。他认为艺术即表现,美学即语言学,他所说的语言并不是作为符号的媒介,而是与逻各斯同质的广义的语言,即各种能够表现心灵的声音、线条、色彩等精神形式。也正是因为对媒介符号的否定,克罗齐的艺术才能作为主体靠近纯粹实在的中介,主体经由直觉表现而抵达对宇宙无限的理解与把握。克罗齐美学的逻各斯思想背景对于中国的接受者无疑是陌生的。中国传统哲学中“立象以尽意”的象征思维,即借助于某种具体有形的物象来表达一种无形而抽象的理念与意义,体现在艺术中便是有形之物质媒介的不可或缺,艺术传达符号媒介作为表现艺术家心灵中的情感与理想的中介,是中国美学家们在谈论艺术时不能省略的一环。虽然作为一种有形的符号并不能完全而彻底地表达意义,但是中国传统美学中一直强调“言外之意”与“象外之象”的无穷延展,这也正是中国美学的独特韵味。这种文化传统的差异很明显地体现在克罗齐美学在中国的接受之中。
再者,审美活动与人性结构有着内在的联系。人性结构是由理性与感性两个层面构成,理性体现为抽象思维,而感性则与人的情感直接相关。在理性与感性的相互作用中,审美活动才得以生成。中国美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实际上是个体感觉与情感逐渐得以丰富与拓展的漫长过程。从宋末明初开始,个体的感性生命突破“天理”的秩序而逐渐得到重视,明朝时期的美学开始表现出与儒家伦理美学精神的背离,它通过对人性情欲的肯定与宣扬,来突出被儒家伦理束缚和压抑的人的内在情感。这种情不是儒家伦理的普遍的情,不是魏晋人的宇宙感怀和人际感伤,而是一种基于个体感性存在的自然情欲,它重视的是个体感性存在中本能动力的价值和意义。克罗齐的接受者们正是在早期美学情感论的基础上,开启对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化实践。他们无一不是从“情”出发,展开对于克罗齐美学思想的接受。虽然克罗齐早期的美学思想中,并未突出“抒情”的重要性,但是这并未引起中国接受者们的足够关注。即便是作为《美学》译者的朱光潜,也对克罗齐前后期美学思想中抒情意识的逐步增强不以为然。或者可以说,接受者们正是因为克罗齐后期的《美学纲要》中对抒情的强调,才得以靠近并接受克罗齐美学的。这也足以说明,他们是从克罗齐的抒情表现主义中,发现了与中国传统美学的内在一致性。正是借助于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使得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表现主义因子被激活,从而在现代语境中得以彰显和突出。而且,克罗齐美学的接受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克罗齐的情感表现论进行了拓展与改造,并将之运用于不同领域的理论建构中。和彻底西化派与传统派不同的是,克罗齐的接受者都注重提取传统文化中的情感与生命元素,而克罗齐美学正是他们提取这些元素的参照。或者可以说,正因为克罗齐的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对感性生命的重视,使得他们选择了克罗齐。每个接受者都试图寻找克罗齐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衔接,比如林语堂发掘了中国传统浪漫主义文学的性灵,滕固和邓以蛰关注传统艺术论中的气韵生动,朱光潜则从中国传统诗学中发掘出与克罗齐表现主义近似的诸多要素。
最后,克罗齐的心灵哲学将艺术与人的理智认知能力、经济活动与道德意志区分开来。克罗齐并非不明白艺术难免会渗透进现实经验的元素,但是他要寻求的恰恰是在逻辑思辨上保证艺术的独立性与纯粹性,而他的良苦用心似乎并未获得中国接受者们的充分宽容和理解。无论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的美学,都不在人与自然、概念与实践、思维与行动之间作严格的逻辑区分,人的精神活动始终与经验世界紧密连接在一起。这一根本的文化思维前提注定了克罗齐美学在中国被改造的命运。他的纯粹精神领域的直觉表现或艺术不可能在中国文化中落地生根,它必须从纯粹精神的领域落实到现实人生,才能得以传播与接受。而且,克罗齐一直强调与艺术绝缘的道德世界和经验世界,都被中国的接受者们将之与艺术作了一定程度的结合。克罗齐的接受者们都积极介入公共生活,主张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改造国民性与拯救民族危亡并存。无论他们借助于克罗齐的思想多么强调文学艺术独立于道德与意识形态,但是其文艺美学观念总是不自觉地指向现实人生与国民性的改造以及道德伦理的完善,最终的理论落脚点依然是现实尘世而不是超越的精神世界。无论是朱光潜和林语堂,还是邓以蛰和滕固,他们在建构艺术理论的过程中,始终不忘强调艺术改造人生与社会的现实意义。换言之,他们接受克罗齐美学,不仅仅在于解决美学与文学批评的问题,而是要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危难时刻,借助艺术,达到改变人之精神面貌,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正因为这些文化差异与冲突的存在,克罗齐美学在翻译与接受的过程中,“误释”和“误读”就不可避免。翻译不仅仅只是语言符号之间的机械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碰撞与调和,它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叛逆”的过程,不可能求得意义的完全对等。在概念汉译中,译者首先要找寻中国语言文化中与西方概念意义相近的语词,或者创造新的语词,无论是现成的抑或是新造的语词,都会带来西方概念原有意义的缺省与增补。与其说这是一种“误译”或者“误释”,倒不如说是一种叛逆的创造,它带动了西方文论在中国文化语境里新的生长。理论的接受更是一个观念和思维之间的对接与磨合的过程,不仅需要在现实观念上获得接受和认同,而且要在历史文化和传统意识中得到共鸣与应和。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