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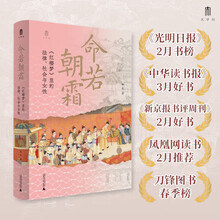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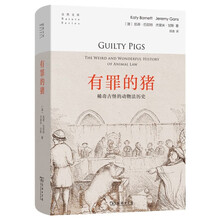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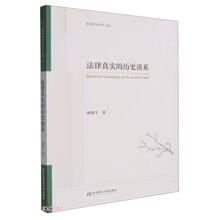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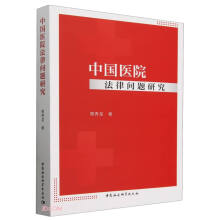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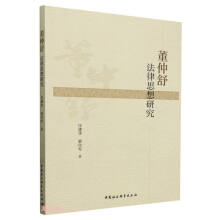
1. 法律文化学者、《法律讲堂》资深主讲人柯岚教授全新力作,从法律社会史角度解读《红楼梦》。学者梁治平、林少阳、邱澎生、俞晓红推荐。
2. 聚焦十二位(类)女性角色,对应十二个清代法制问题。本书共十二章,每章聚焦一个《红楼梦》里女性命运的典型,如秦可卿、林黛玉、尤家姐妹等,分析她们如何因连坐、拐卖、生育、家庭财产分配等事件而陷入法律困境,进而被推上绝路。严酷的“亲属相奸罪”,使得秦可卿遭受尊长侵犯时选择了自尽;法律对女性继承权的苛刻限制,开启了林黛玉与尤家二姐妹的悲剧命运……
3. 依据真实司法案例,剖析清代女性困境的制度性原因。清代法律如何制度性地决定了女性地位的低下?这些深层的制度性缺陷又如何成为曹雪芹绝望的根源?本书通过整理与《红楼梦》中事件类似的清代司法案例,揭露当时法制现实之下的深层结构,如封建等级制度、妇女结构性失权等,这些社会问题不仅是小说悲剧的根源,也是当时大多数人困境的根源。
4. 从“法学与文学”研究途径,为红学研究提供新意。作为长年钻研清代法律与社会的法律学者,柯岚教授透过分析《红楼梦》作者及书内角色如何受到当时法律的限制、如何作出反抗与批判,来还原已消亡的法律对彼时社会生活和艺术创作的影响,让我们对《红楼梦》有了更为丰富而真切的理解。
5. 多角度剖析清代法律与社会问题,窥见清代社会生活。本书解读《红楼梦》中角色的法律困境,既列举法律条款和案例,也联系《红楼梦》成书问题、作者身份问题,还综合清代制度史、经济史、人口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一个立体、动态的清代社会。
6. 史料翔实,举证严谨。本书不仅使用大量来自《大清律例》《清会典》《刑案汇览》的材料,还从清代的奏折、起居录、笔记、地方志等文献之中整理出相关的案件记录和议论,并综合汉、晋、唐、宋等朝代的法律和案例展开分析。
编辑推荐
(一)为什么叫“命若朝霜”?
书名“命若朝霜”取自曹植“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其中无可奈何苍茫悲凉种种,与本书分析《红楼梦》里诸女子的命运基调相似。如果把《红楼梦》看作迷宫,柯岚教授这本新著《命若朝霜》就可以看作从法学角度撰写的迷宫攻略,通过这本攻略我们会发现,在《红楼梦》里的世俗世界中,给女性角色准备的所有路都是死路。曹植和曹雪芹都经历过很多生死,从法学的角度,能分析出他们的时代对人命的认知、态度等都与我们有极大不同,而从文学的角度,我们仍能强烈共情他们对人命的哀悼。
(二)为何她们只有选择自尽才能有机会递出诉状?
《红楼梦》写了很多女性角色之死,诱因和致命因素各不同,作者似乎在穷举当时女性的绝路,仅自杀手法就有悬梁、撞柱、投井、刎颈、吞金……我们为之震撼和悲哀,但仅凭感性的直觉,其实很难真正理解她们的绝境。
以前常读到这样的句子,大意是某位角色用自己的死控诉某种黑暗与不公,多半以为是比喻和抒情。书中,柯岚教授写到秦可卿、鲍二家的、尤家姐妹等角色之死时,结合当时法制现实分析,论证了她们以自己的死为诉状来控告侵害者的真实可行性。还举出很多清代司法案例,联系《红楼梦》的情节,作者指出,当时的特权者对普通人的人身、财产等权利的侵害都几乎受到法律保护,受害者只有当即自杀,递出控告对方“威逼人致死”的诉状,才有可能为自己讨回一点点公道。
了解《红楼梦》的法制背景之后,再去看其中角色的自杀,才能理解他们的死,多半不是一时悲愤的冲动之举,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抉择,他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死亡事件上。
(三)从《红楼梦》看清代女性如何应对性侵害
在《红楼梦》成书的时代,因为法律、制度、社会道德规范的限制,女性受到性侵害时,尤其是受到地位比自己高的男性的侵害时,完全没有救济途径。《大清律》明文,说强奸罪受害者“邪淫无耻”,还要求受害者必须有“损伤肤体,毁裂衣服”等能证明自己全力反抗的证据,当时就有人指出这样的法条在实施时“势必以自尽者为强(奸),而不自尽者为和(奸)”,其实就是逼受害人去死。
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性侵害在清代是个显著的问题,尤其是家族长辈对晚辈妇女的侵害。柯岚教授在书中分析到,由于法律明文规定长辈对晚辈的特权(比如“干名犯义罪”),遇到这种事,无论受害者当下是顺从还是反抗,无论是自己报官控告罪犯还是被人发现而报官,受!害!者!基本都是死罪,罪犯反而有许多机会轻判。
不过若实在倒霉遇到这种事,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如果我们在发现上位者有侵害意图时立即自杀,那么不仅清白得以保全,还同时递出了自己的诉状,罪犯将因此(有一定的概率)受到(并不重的)惩罚。
清代法律如何制度性地决定了女性地位的低下?这些深层的制度性缺陷又如何成为曹雪芹绝望的根源?
本书从法律社会史角度解读《红楼梦》,聚焦十二位(类)女性角色,对应十二个清代法制问题,整理与《红楼梦》中事件类似的清代司法案例,剖析清代女性困境的制度性原因,考察了清代性别、家庭、法律、政治间的互动与演变。作者综合多重视角,立足“法学与文学”研究路径,聚焦人口拐卖、生育、财产分配、官员考核等社会议题,分析了《红楼梦》作者及书内女性角色如何受到当时礼教与法律的限制、如何做出反抗与批判,展示了清代法律与社会的风貌。
结合《红楼梦》成书时代的法制现实可以推断,书中对十二伶的如何“低贱”的描写,可能是为读者想象十二钗的未来命运提供素材。而甄英莲作为第一位出场的少女,她的命运预言了大观园所有少女的命运:“无依、易主、早夭。”
——编者按
《红楼梦》的悲剧是一个法律事件:贾府家长犯重罪,按当时的法律,大观园的少女们很可能都会成为别人家的奴婢
在曹雪芹生活的时代,自杀、出家、卖为奴隶其实是籍没刑罚所及的罪人女性家属最常见的三种结局。曹雪芹的家族是在雍正五年(1727)被雍正皇帝抄家的,因为曹家没有政治罪行,只有经济罪行,受到的惩罚是比较轻的,只没收了财产,没有家属被没为官奴或变卖。但不是所有获罪抄家的人,都能得到这样的从宽处罚。
《红楼梦》中女性自杀现象很常见,前八十回就有很多女性自杀。从第五回金陵十二钗判词和《红楼梦曲》透露的线索来看,八十回后真本中,十二钗也会有不少自杀。当贾府还没有覆灭、大观园还能受到园外贾府的保护之时,大观园中有些少女尚且因为各种原因选择自杀。等到贾府彻底覆灭时,她们会成为毫无法律保护的极度弱势群体,会被当作罪人的财产一样计算籍没,可以想见,她们当中身份最为高贵也是最为缺乏生存能力的群体,面对这样的惨祸时,自杀会是极为自然的选择。
在清代,犯罪大臣的家属被判籍没流放边塞的,女眷在流放前自杀是常见现象,家人为了让她免于受辱,甚至会要求她自杀。
清代史料《永宪录》记载:雍正十二年(1734),河南学政俞鸿图被上司弹劾贪赃枉法,“上震怒,逮问籍没,妻先自尽,幼子恐怖死”。俞鸿图被逮捕下狱审问,其家被判籍没,消息传来,刑罚还未施行,他的妻子就自杀了,小儿子被吓死了。
雍正三年(1725),年羹尧因罪被抄家。户部侍郎汪霦之子汪景祺为年羹尧幕僚,曾随年至青海军中。汪景祺作《读书堂西征随笔》阿谀年羹尧,其中有一篇文章《历代年号论》论证“正”字为年号凶字,有“一止之象”,指出历代年号带“正”字的皇帝多没有好下场。因此触怒雍正,汪被判大逆罪,枭首示众,阖门遭难。其兄弟、子侄有在做官的全部革职,发配宁古塔。五服以内之族人有在任官及候选候补官的,全部革职,原籍地方官负责看管,不许出境。其妻发配到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永宪录》中记载:
(景祺之)妻巨室女也。(一云。大学士徐本妹。)遣发时。家人设危跳。欲其清波自尽。乃盘躃匍匐而渡。见者伤之。
汪景祺的妻子是大家闺秀,父兄都是高官,家人看她遭此命运,不愿意她到黑龙江受辱,她发配启程要坐船,家人就故意把上船的踏板弄得很危险,希望让她落到水里自尽。但她不愿意死,她不愿意受丈夫的牵连为他殉葬。她走到那踏板前,就俯身趴下来从踏板上慢慢爬过去,旁观的人们无不伤心落泪。没有更多史料记载这个不知名的弱女子后来的经历,可能她慢慢爬行的时候最后还是落水死了,也可能她躲过了这一劫,去到黑龙江极度寒冷的军营,沦落风尘苦苦求生。
雍正四年(1726),礼部侍郎查嗣庭因在任江西乡试主考官时所出试题也涉及“正”“止”字,“讽刺时事,心怀怨望”,下狱治罪。次年三月间,查嗣庭次子查克上在狱中病死。查嗣庭为保家人性命,在狱中自杀以谢罪。同年五月雍正下旨:查嗣庭犯大逆罪,本应凌迟处死,因为已在狱中自杀,戮尸砍头示众。其子查沄已在十六岁以上,本应处斩立决,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其家女眷(包括母女妻妾、其子之妻妾)、其余子侄及其兄查嗣傈均流放三千里,其兄查慎行年老,不知情也未参与,从宽免于追究。于是查家女眷面临了和汪景祺妻子同样的绝境。
查家是书香世家,家风严正,查家妇女都很有血性。清儒方苞记载,查嗣庭的妻子史氏在流放令发来当日对家人说:“诸孤方幼,我义不当死,但妇人在,难历长途,倘变故不测,恐死之不得矣。”这话凄惨之极,可见当时查家遭遇的是怎样的飞来横祸。查嗣庭次子查克上已在狱中病死,他的妻子浦氏听见婆婆这样说,悲痛欲绝,回答说:“我遭遇与姑(古代指婆婆)同,当与姑同命。”就写下绝命诗,把孩子都托付给她的父亲,和史氏一同自尽。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中记载,查嗣庭一女善诗,在流放途中驿站题诗哀叹:“薄命飞花水上游,翠蛾双锁对沙鸥。塞垣草没三韩路,野戍风凄六月秋。渤海频潮思母泪,连山不断背乡愁。伤心漫谱琵琶怨,罗袖香消土满头。”
罪人的女眷假如没有选择自杀或出家,则会被当作财产一样变卖,沦落到社会的底层。她们在遭难之前,养尊处优、锦衣玉食、毫无涉世经验,一夜之间,就从社会的最上层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家族原来在政争中结下的对头,甚至家族内部原有矛盾造成的仇隙,都可能导致有人在此时落井下石、趁火打劫。而家族中的女性往往成为报复行为指向的对象,即便没有因罪被牵连卖为奴隶。但家中男性获罪以后,她们丧失了父兄的保护和经济支持,也可能被奸人变卖为奴。
曹雪芹主要生活于雍正、乾隆年间,他13岁时被抄家,后来亲戚朋友也有多人遭遇差不多的命运。抄家本来就是极度残酷的刑罚,即便还没有被最终处刑,家人是否被株连还不确定,抄家之时家人都有可能选择自杀。在雍正乾隆朝,曹雪芹应该见闻过太多官员被判籍没、家人被流放被迫自尽的人伦惨剧,甚至他自己熟识的人家,都有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有些人家处事慎重的,也可能在惨祸来临之前让女性家眷出家躲避。金陵十二钗未必见得人人都有原型,然而作者必然是经历见闻了很多女性的悲剧故事,才写出了《红楼梦》中“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性众生相。
——选自柯岚《命若朝霜:〈红楼梦〉里的法律、社会与女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序
引言:《红楼梦》记录了宗法社会中的女性悲剧
第一章 甄英莲的命运与清代的司法黑暗
第二章 秦可卿之死与清代的亲属相奸罪
第三章 赵姨娘的诅咒与清代的巫术犯罪
第四章 宝黛悲剧与清代的婚姻继承法制
第五章 宝钗结局与清代的选秀制度
第六章 鲍二家的之死与清代的仆妇贞节
第七章 王熙凤管家与清代的宗族治理
第八章 探春治家与贾府的陋规
第九章 尤三姐之死与清代的定婚法制
第十章 尤二姐之死与清代的妻妾宗法
第十一章 红楼伶人与清代的查禁女戏
第十二章 十二钗的结局与清代的籍没刑罚
后记
温馨提示:请使用罗湖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本书是一部文学、历史与法律的跨学科研究之作,作者透过《红楼梦》这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学经典,为我们展示了清代法律与社会的风貌,同时让我们对书中各色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行为与命运,有了基于制度与文化的深刻理解。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理解,作者笔端的同情与批判既内在于历史,又超乎时代。
——梁治平(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中西书院&光华法学院全职兼任教授,“法律文化研究文丛”主编)
清代法律如何制度性地决定了女性地位的低下?这些深层的制度性缺陷又如何成为曹雪芹绝望的根源?就这些问题,作为法律学者的作者以其深切的同情,揭示了一个“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性命运世界。本书展示了作者纤细的文心、深邃的史识和深切的关怀。法律社会史角度的《红楼梦》解读,也许是作者对前辈学者萧公权、瞿同祖相关论著的呼应、补充。本书兼有法律史、社会史、政治史和文学的视角,它令人再次感觉,《红楼梦》是一部有情、可感、有细节的信史。
——林少阳(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南国学术》主编)
《红楼梦》研究著作早已汗牛充栋,柯岚教授立足“法学与文学”研究途径,再为红学研究提供新意与胜义。她既提醒法学界:法律“教义学”的解释方法很难深入理解古代法,只有当时文学作品才能;也呼吁文史学界:面对古代人物和社会现象,如果“完全脱离当时政治法律的限制”去作“以今度古”的阐释,推论内容恐怕也容易显得“苍白甚至荒诞”。作为长年钻研清代法律与社会的法学家,柯岚教授渴望揭示《红楼梦》作者及书内人物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当时礼俗与法律的限制,还有他们对当时法律与社会礼俗的反抗与批判。作者深信:“只有了解曹雪芹生活时代的法律与社会,《红楼梦》才可能得到更为丰富而真切的理解。”这是继萨孟武《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之后,另一部能够深入考察清代性别、家庭以及法律、政治之间有机互动与复杂演变关系的难得佳著。
——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法制史研究》总编辑)
法眼观红楼,厘清疑案罪因,莫过香尘落定时,冷观处见大悲悯;
律科说情纪,辨正陋规巫术,奈何花魄飘零久,平说中闻小惊雷。
——俞晓红(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红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