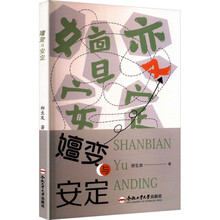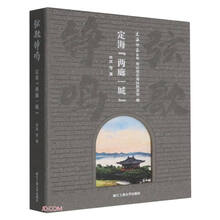《冬去春来/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
东方还远没来得及呈现出鱼肚白,翠山山腰处传来了一声枪响。这裂帛一般的声响,让这个原本安静沉睡着的山坳有了一丝轻微的颤动。几只胆小的鸟像子弹般弹起,漫无目的地朝远方空旷的夜空飞去;山脚下一条耳尖的狗发出几声不明就里的狂吠,随即犬吠声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
习芳母子俩都被犬吠声惊醒,儿子开始哇哇大哭起来。习芳只得将儿子抱起,一边轻轻拍着他的后背,一边轻轻地拉开了窗帘。窗外什么都看不见,但偶尔还能清楚地听到鸟飞的声音。没几分钟,儿子趴在自己的肩膀上睡去,习芳慢慢地将儿子放到床上,自己也在旁边躺了下来。儿子哼了两声,并蹬了几下;习芳摸了一下尿不湿,还是干的,又把滑脱的薄毯子重新给儿子盖上。
听着儿子轻微的呼吸声,习芳摸到了床头的手机,看了下时间,凌晨三点十七分。在手机的亮光中,习芳看到了靠衣柜放着的大袋子,拉链还敞开着。习芳想起了四天前的下午,父亲帮忙提着这个大袋子送自己上车时的情景,而明天她就要回石头镇的娘家。迷迷糊糊中,习芳又睡着了。
三个小时后,天渐渐地亮了起来,石家坳,这件像是被时光漂白后高高晾挂在砂子镇东南角的旧短袄,也开始有了风吹草动。早一个星期连续下雨,使得春插一拖再拖,这几天天气才转好,村民们像是跟时间赛跑般,把一年的希望种下去。山脚下、山坡上,点缀些戴草帽、挑箩筐的男人;妇女们有的在洗衣服,有的燃起了炊烟。山脚下的小溪,像是调了闹钟一般在晨曦中醒来。
砂子镇地处化安县的最南边,大小不一、高低不齐的山峦肆意侵占,使得这里的耕地面积寥寥无几,而且还带来了交通的闭塞,化安县火车站也是近几年才有的新鲜事物。二十几年前,那时的砂子镇还叫砂子乡,每天前往化安县城的汽车也就上午下午各一趟,一路上还像个醉汉一样跌跌撞撞。石家坳的村民如果想坐早班车去趟县城,一大早就得起床,提着马灯或者打着手电走上一二十里山路,当他们赶到砂子乡汽车站时,早已精疲力竭。如今,住在山坳里的村民多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大都在外面打工,他们只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的时候才回来。
如果用力把时间的大磨往回推个十年,举出石家坳哪家最困难,可能会有不少村民认为是石智勇家。那时,已丧偶六年的石智勇靠着两分薄田和几株比自己还瘦弱的茶树与命运抗争着,背弯得如一张紧绷的弓,蓬松的几根乱发如早秋的芦苇,没穿过一身干净的衣裳,没趿拉过一双像样的鞋子,甚至一次也没去过化安县城,他对化安县城的了解像是拼图一样,是从后来在县城打工的小儿子秋生那里一点一滴艰难地拼凑起来的。
石智勇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春生,小儿子叫秋生。他常想,自己要是有一个闺女就好了,这样的话,一年到头也能到闺女家走走,也不至于跟一棵老树一般一辈子固守在一个地方。去年早春,还不到五十九岁的石智勇终究没能跟上时间的节奏,也未等到孙子的出生,就倒在自家的厨房。
在旁人看来,石春生和石秋生不像是两兄弟。哥哥春生长得瘦小,其貌不扬,小时候的一场病还让他落下了聋哑的残疾,如今,三十八岁的他独自守着半山腰上一年半前造的这栋两层小楼,平时除了上山护林,还下山种地。弟弟秋生比哥哥春生小了十岁,长得高大魁梧,全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在家时就是一把种地好手,如今,已在化安县城打拼了十年。
如果说春生的那场疾病,对当时本来就贫困的石智勇夫妇来说是雪上加霜的话,那么,秋生的出生无异于是雪中送炭,总算是给了石智勇夫妇一些安慰。虽然秋生从十八岁起就一直在县城打拼,而春生一年到头守候在石家坳,但兄弟俩的感情一直很好。
习芳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窗户,满眼绿色簇拥而来,与她撞个正着。天空少云,似乎预示着今天是个好天气;鸟啁啾着,像是已经从先前的恐惧中缓过神来。正值春天,石家坳呈现出它一年里最美的样子,一切都像是新生的,完成了对刚刚过去的冬天的颠覆。院子的西边,公婆的坟头新长出的草,似乎在宣示着新的季节不可逆转的到来。
头发蓬乱的习芳在梳妆台前坐了下来,感觉自己睡眼惺忪,全身乏力。在镜子里,她看到了仍在熟睡的儿子。来石家坳的这几晚,儿子的睡眠质量都不怎么好,光是昨晚,就醒来过好几次,哭闹过好几回。是儿子住惯了石头镇的外婆家吧,习芳这样想。没多久,屋后瓦砾路上传来老水牛的脚步声,习芳知道,那是大伯子春生喂牛回来了。
喂完牛的春生还骑着电瓶车去了一趟镇上,买了些菜回来。春生一个人在家时,都是随便吃点什么,现在弟媳来了,总得多弄两个菜。习芳想,自己大老远从娘家跑来,本想给春生帮点忙,早点结束春插,现在倒好,不但没帮上忙,反而添了麻烦。早饭后,春生到田间去了,洗晒好衣服的习芳坐在堂屋里,看着怀中的儿子发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