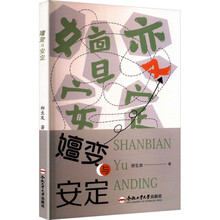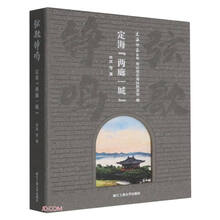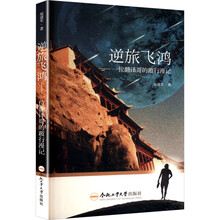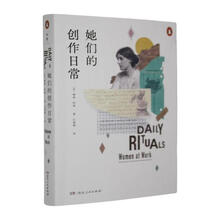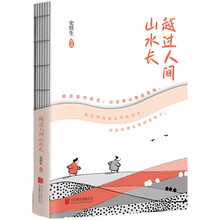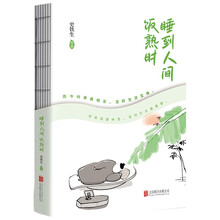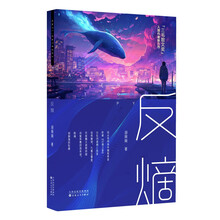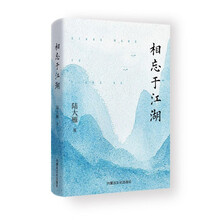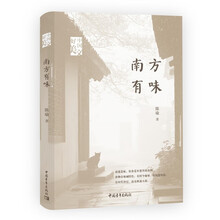春山多胜事
“春山多胜事,赏玩夜忘归。”照理说,物流之便捷,使远方异色瞬息可达。这些花草,或雍容,或清逸,常置案头,在审美感受上,本应满足。可是偶尔回一趟乡下老家,邂逅山边一朵野花之后,寂然远虑的幽情,便绵绵不绝,当年玩赏忘归的胜事也一一浮现了。
“立春一刻,百草转折。”乡谚告诉我们,立春一到,蛰伏一冬的草木都欣欣然睁开眼,然后抽芽、拔节、抽须;含苞、吐蕊、结籽,一切都按照上帝画就的图谱争先恐后,抖擞精神,吐露芳华了:
黄栀开花白娘子,
柴彭开花满山红;
百合开花喇叭响,
枧槭开花白蓬蓬……
乡间没有《诗经》,“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可以通过歌谣民谚做到。故乡三面靠山,一面临海。矮山丘陵、地头田角,都是童年的“博物园”。朝夕相伴,那些卑微的山野小花,便会成为你童年的伙伴;当你历经世故、厌倦人情之后,偶一回眸,那些圣洁的小花仍然在你的生命花园里静静开放。
“黄栀开花白娘子”,说的是黄栀花花色玉白,犹如美人。作为观赏植物的栀子花,百度上的介绍复杂而无趣,在我的记忆里,这种喇叭形的六瓣小花,花色纯白,花蕊有着浓郁的芳香。女孩子上山砍柴,往往喜欢带枝折来,插在瓶里,灌以清水,以作案头之供;或梳洗方罢,插一两朵在发辫间,白玉幽香,随风轻扬,贫瘠的生活里便会多出一丝芬芳。但是,男孩要是摘一朵黄栀花来嗅,那是要被同伴们耻笑的:“嘿,女人相貌!”当然,嗅花是女性化动作,但黄栀花椭圆形的果籽,是我们男孩的钟爱。剥开表皮,深黄的籽儿是很好的颜料。于是,我们就拿着果籽,在家里的板壁、村口的墙壁上涂鸦,驰骋我们的艺术想象。那个时候,你翻开我们书页打卷的课本,一定会发现,那些黑白的画,都被我们“着了彩”,买不起蜡笔,黄栀花籽就是我们这些马良手中的“神笔”。宋朝杨万里有诗《栀子花》:“树恰人来短,花将雪样年。孤姿妍外净,幽馥暑中寒。有朵瓶子,无风忽鼻端。如何山谷老,只为赋山矾。”杨万里把黄栀花的枝、花、果、香,都作了逼真的描摹,并抒发了为歌咏“山矾”(黄栀花),宁愿老于山谷的心思。士大夫的趣味,毕竟不同于我们的纯真,我们的女孩只用它装扮单调的青春,而我们男孩,则拿它挥写肆意的想象。
柴彭花,即杜鹃花。清明时节,漫山遍野,满目红艳,故日“柴彭开花满山红”,所以也叫“映山红”。论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杜鹃花堪比菊花、梅花、牡丹、荷花等名花。近来时兴旅游,“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高山杜鹃、原始森林杜鹃不时见诸报章,游人趋之若鹜。但于我而言,杜鹃花与儿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先,它几乎不是作为一种花而存在的。杜鹃含苞,乃在冬末时节。冬天里的杜鹃,我们称之为“柴蓬脚”,砍下来晒干,是极好的烧火材料。大冬天里,我们呼着白气,搓着双手,要上山斫柴,柴蓬脚、枧槭、壳捏红等灌木都是我们首选的“硬柴”。随着季节转暖,我们的柴捆里渐渐多了含苞初放的柴蓬脚。“吹面不寒杨柳风”,几阵东风过后,山坡上的杜鹃花,便如摄影师手中的快镜头,豁然红成一片。“秀色可餐”这类词语,是我们多年以后,饱食终日之余的调侃,但当年这些火红的喇叭花,确实是可以吃的。在我少年时,吃杜鹃花的花瓣乃是常事。我们把花形完整、花瓣鲜嫩的花拔下来,里边的花蕊会自然留在枝头上,吹一吹,就往嘴里送。大人叮咛过,吃了杜鹃花的花蕊,是要变成聋子的,于是我们只吃花瓣。杜鹃花花瓣酸中带甜,汁液殷红,吃多了以后,花青素会把嘴角和牙齿染成紫红,于是这些孩子就带着满嘴的紫红挑柴回冢。
真正以欣赏的姿态面对一朵杜鹃花,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了。每年清明节,如果是个艳阳天,祭扫祖先便变成了踏春郊游。我们跟先人的约会,再也没有杜鹃泣血般的哀戚,反而成了一年一度的聚会。砍掉坟茔上的柴草,清理墓碑前的平地,然后念念有词地排出东海鲜鱼、山里毛笋、两瓣豆芽、清明麻糍,沥一壶酒,焚一炷香,双手合十再拜,先人便来宴饮了。这时候,满山遍野,杜鹃盛放。我们会折一大把搁在先人的坟前,算作心香一束。有些女孩还会折来很多杜鹃,装扮坟茔。遇到根株健硕、含苞又多的杜鹃花,我们会连根挖起,移植于庭院。如果照顾得好,当年就会开花。李白诗云:“杜鹃花开春已阑,归向陵阳钓鱼晚。”如今,人到中年,偶尔上山,已经抛却刨根挖蒂的心念,习惯于对着一朵杜鹃花微笑了。
在我的少年时代,因为黄栀花和柴彭花的普通,遇见它们并不会让我们惊喜,真正让我们窃喜的是发现百合花和兰香花(即兰花)。现在人工培植的百合花,红、黄、白、粉,花色多种,一茎单头、多头的皆有,什么卷丹百合、美丽百合、山丹百合,不一而足。可在当年,在柴草纷披的山坡上,突然见到一株百合卓然独立,临风摇曳,那是多么惊艳的事情。我会披荆斩棘,急匆匆地来到百合的跟前与它对视。你看它的茎秆,一般有五十来厘米长,表皮淡紫色,柳叶状的青叶从底到梢,从小到大,犹如碧玉,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