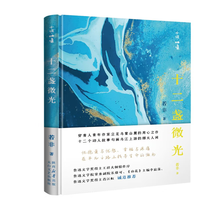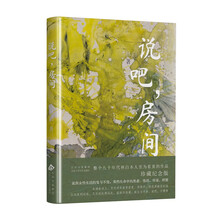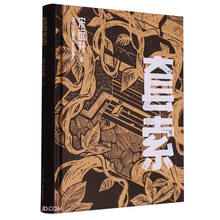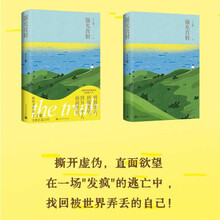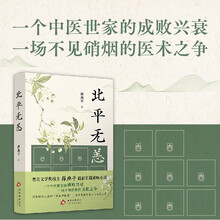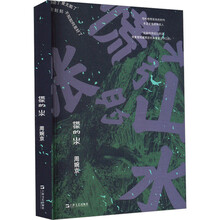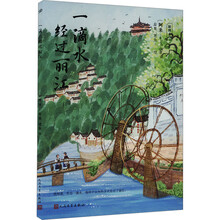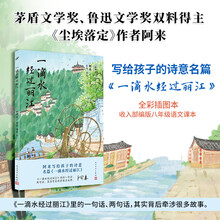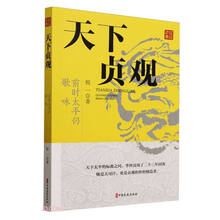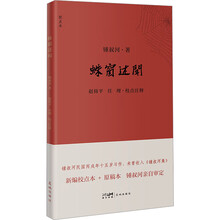一、莫失莫忘
长安城内,坊内茶馆的闲人们沿着朱雀大道眺望,天上一阵阵的箭矢划过。
“这大唐才不到十年,又不太平喽。”任侠们嬉笑,“这次又是谁啊?”
“照我看,指定是天策府!”
他们躲在朱雀大道两旁的坊中私语,一队人马沿着大道向着城外冲杀而过,为首的人是齐王府副护军——薛万彻。此时此刻,薛将军失了平日的嚣张,失魂落魄的,而他身后数十名骑兵,也个个灰头土脸,劫后余生似的。
不久之前,随着太子和齐王被杀,东宫及齐王府迎来了终局。失去了效忠的对象,护卫们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前途先抛到一边,为了不失节,或者说为了保命,这二者其实是一致的,薛万彻等人只得先逃出长安,再做打算。
视线重回长安,那泼皮嘴里的“不太平”并未发生,至少争端始终被限制在了坊市之外。
“看来胜负已分。”一老汉抚须,“在‘兄弟阋墙’上,本朝还是要远胜于前朝啊!”
“老丈,你这话忒不地道。”一文士哼笑一声,“前汉巫蛊之祸,长安死伤数万。与之相比,今日我等岂不幸哉?”
说书的人最爱这种戏码——太子对诸侯王,兄弟再度阋墙。舞台一样,仍是长安这座城;结局也一样,仍是次子压长子一筹。二者仅有的区别,在于隔了一辈人、两个朝代、将近三十年后,争储的人心意变了副模样。
当磊落的李世民和矫饰的杨广面对相同的处境,二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决定。前者选择了亲赴战场,沾上兄弟的鲜血,用手中的弓箭把事件终结;后者选择了借刀杀人,在获得父亲的信任后,用谎言让事件落幕。
人人都爱主角亲力亲为,没人喜欢虚伪的故事。正因如此,在当代和后世评论家的笔下,李世民比杨广更富议论性,他成为太子这件事也必将招来更多的揶揄。
不过,此时的李世民对此丝毫不在意。作为最终的胜利者,他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填补权力真空。这不光是秦王集团的集体目标,也是为了不让刚刚恢复的山河因此流血。毕竟事已至此,万不能让父亲成了晚年的汉武帝啊!
以雷霆之势将太子残党清洗完毕后,仅仅一日之内,长安便温温和和地换了天。玄武门之变当天午后,朝廷的诏就奔向了天下各道:大赦天下,归罪太子。天策府的学士们顷刻间发挥了巨大的力量:罪孽止于皇家,余党再不过问。
一句“再不过问”,应了文士的“岂不幸哉”。除了必死之人,每个人都是幸运的。先前逃出城的薛万彻等人是,在城中议论的闲散之人也是。
“上至尧舜禹,下迄隋炀帝,纵观国史,”那位文士叹息,“此间三百年,用陶潜一言足以蔽之!”
“何句?”
“白日沦西阿。”
“瞎!三代以降,千年以来,毁冠裂冕不可胜数,又鲜有经天纬地之人。”茶馆博士跟着叹口气,“叫这白日怎能不沦西阿?”
“我倒是希望,除了这等宫廷之事,本朝也能远胜于前朝。,’文士又道,“可这世上,善用人者多而平天下者少,能上位者多而知为君者少,成帝业者多而善治国者少……”
“这位明公,请喝茶。”
玄武门之变后第三天,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同日下诏将国事处决权交由太子,皇帝本人则退居幕后,只闻奏、不与谋,再不管天下。
李世民成为太子后,天策府属紧随其后,人人得以更上一层楼。文官们以长孙无忌、杜如晦、高士廉、房玄龄四人为例,长孙与杜位列左庶子,高、房位列右庶子;武官们以尉迟敬德和程知节为例,二人分别担任太子左、右卫率;十八学士中,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
虽然这只是东宫的人事安排,但人们很清楚,这就是未来的朝堂格局。换句话讲,等到太子登基即位,大唐的庙堂诸公,约莫也就是这些人了,他们将在之后的十数年中深刻影响整个大唐。
自己人都安排妥当了,该处理那些原先的“敌人”了。“一无所问,,的承诺自然作数,然而罪可以不问,但人不能不用。尤其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失败者”,李世民绝不愿因权斗而偏废之。
武德九年中,统一战争只占四年,权力斗争却占了五年。由此能看出,东宫和齐王府着实不是什么草台班子,不然秦王早就得了手了。齐王府暂且不论,太子李建成的朋党中,有一位最知名的人士——魏徵。
魏徵作为前东宫洗马,曾三番五次向李建成进言,譬如建议太子代替秦王平刘黑闼等。除此之外,魏徵还是东宫中为数不多的清醒者,他时常劝说太子切莫妇人之仁,以免夜长梦多……这些“罪行”,魏徵清楚得很。他是原东宫“奸党”的头号,是兄弟阋墙“祸水”的源头。他跟旧太子绑得太死,只有等新太子来索命。
P2-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