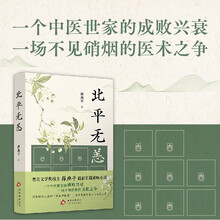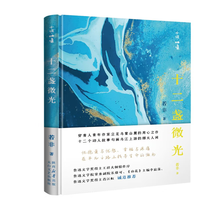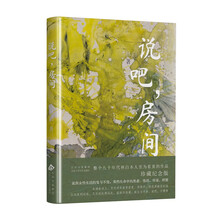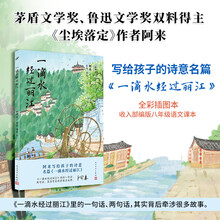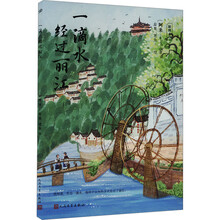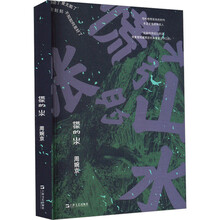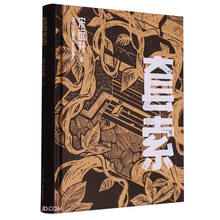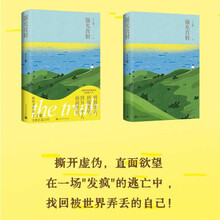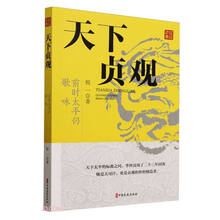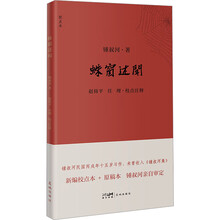《图像天津与想象天津》:
《北洋画报》封面对戏剧女明星的青睐,也与坤伶界的兴盛直接相关。在民国初年以刘喜奎、鲜灵芝、金月梅等进京女伶为代表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过去之后,坤伶界长期陷入低潮,直到1920年代中后期才重新崛起,并且人才济济,出现了雪艳琴、章遏云、新艳秋、胡碧兰“四大皇后”和孟小冬这样大红大紫的女老生,迎来了其“中兴时代”,再度繁盛一时。而且这一代女伶与前辈相比,在社会认可和职业地位方面都更进一步,1930年元旦北平戏剧界正式允许男女同台合演,这对承认女伶的平等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有意思的是,第一批在北京站稳脚跟并走红的女伶几乎均为天津梆子演员,可以说女伶是由天津传入北京的。这也表明天津与坤伶界的密切联系,以及《北洋画报》对女伶的特殊关注“事出有因”。相反,1920年代末的上海电影界却很不景气,著名影星张织云、宣景琳等纷纷嫁人息影,1930年由杨耐梅作俑,许多女演员到外地转向歌舞甚至戏法表演,真正的电影明星所剩无几。因此,对本地文化的关注与对“明星”的消费需求使得“戏剧明星”顺势而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新兴的封面女郎对读者/观众而言,意味着一种新的“观看之道”,它使得传统的“听戏”变为“看戏”.包含了新的评价标准。对于摄影而言,视觉优先于其他一切官能。当摄影画报以其“物美价廉”的图片开始充当“明星”制造者和推广者,视觉的重要性被极大地突出,明星们在服饰装扮上的争奇斗艳正是服从于这一需要。戏剧封面女郎既然成为明星产业的一部分,自然要承担起明星在女性时尚方面的引领作用,这是她们在“明星化”过程中最直接也最突出的表现。1928年秋冬,名坤伶马艳云和章遏云先后剪短头发,并摄影留念,在《北洋画报》发表,这一举动引发了坤伶界迟来的剪发潮流,孟小冬、雪艳琴、杨菊秋、新艳秋等名伶也纷纷剪发,构成《北洋画报》新一批短发封面女郎。与电影明星、交际名媛剪发相比,这更具有“革命”意义。在平津地区,戏剧女演员作为一种传统职业,羁绊更深,伶界规矩繁多,壁垒森严,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女伶不但在舞台上扮演传统女性角色,私底下也比较保守,从第一代进京女伶不多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她们通过现代摄影技术,留下的仍是传统女性形象,与舞台角色接近。但章遏云等新生代女伶剪发之后,已经与舞台形象逐渐脱离,自我形象更加突出。封面的戏剧明星们完成了“头发革命”之后,在旗袍的长短、皮鞋的款式、饰品的式样等方面也充分显示了她们作为“明星”对时尚的敏锐和自觉,甚至连面对照相机的姿势都是标准“明星化”的。
但在种种明星的标准模式下,戏剧明星仍然展现出不同于电影明星的独特魅力。与电影明星开放、张扬的惊艳形象相比,戏剧明星的气质比较婉约、低调,可以说是更家常的“明星”,而且她们的封面形象具有相应的行业特色,并引发了新的时尚潮流。以“戏剧明星”新鲜出炉的第321期封面为例,图片是杨菊芬和杨菊秋的半身像,其中旦角杨菊秋剪着齐耳短发,穿几何花纹旗袍,而以出演须生为主的杨菊芬则穿戴男式长袍和帽子,俨然男装打扮。这与杨氏姐妹各自的专长有关,在男女同台合演之前,戏班往往培养坤伶姐妹,以分演不同行当,马艳云、马艳秋、马艳芬三姐妹也是如此。这幅照片还展示出戏剧封面女郎的两类主要形象——时装照和男装照。前者以章遏云为代表,其落落大方的闺秀气质给时装封面带来了优美的时尚气息,1929年春节章遏云出演津门,并拍摄纪念照,刊发在《北洋画报》封面(见图6)。这张全身像利用光线的深浅形成了巧妙的色差,章遏云的深色中袖旗袍和黑色鞋袜衬出了手臂和脸部的柔白,而背后的灰色布景使得色彩层次柔和而不突兀,与通常的长方形不同,编者还特别为照片加上了椭圆形的装饰框,更增添了视觉效果的柔美,突显了章遏云的个人气质。男装封面女郎则以孟小冬最为出色,1928年年初,孟小冬的西装照片就曾两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有意思的是,1月21日的《北洋画报》名为“妇女装束专号”,内页刊载的都是摩登女性时装和发型,却以孟小冬时髦俊美的男装扮相为封面(见图7),不知是否暗示了一种新的女性时尚——事实上,1930年代初上海时尚刊物上的确流行起“女扮男装”。但无可否认,男装封面丰富了戏剧明星的时尚元素,尽管孟小冬在戏台上扮老生,但她在封面上穿戴着时兴的西装领带,而且新款眼镜、巴拿马便帽强化了这种摩登形象,这实际上是一位别具一格,兼具俊朗和优美的摩登女郎。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