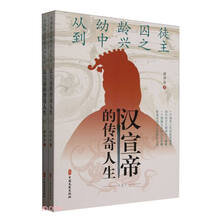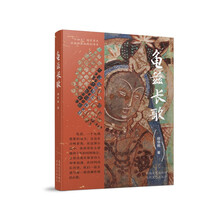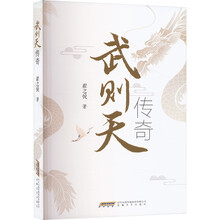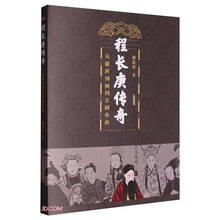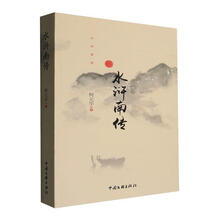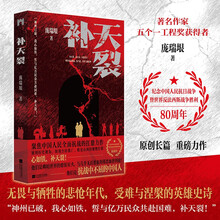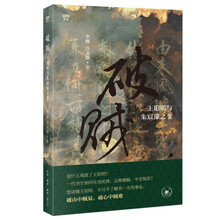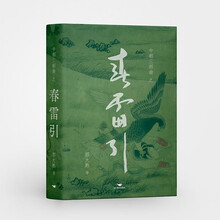第一章 叫天
一见须白心好惨,点点珠泪洒胸前。冤仇未报容颜改,一事未成两鬓斑。
——《文昭关》
师父说:“玉珊,你只等一个机会,就可以重新出山了。”
师父叫米喜子,是真正的名角,尤擅关公戏,在这偌大的京城,鲜有匹敌之人,故有“无米不开台”之誉。师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朝他做了一个劈手,进一步肯定地说:“你的脑后音已经练成了,相信我,只要有个机会,你很快就会红的。”
当时,程长庚正在练戏。他扮着《战长沙》里的关公,手里拿着那柄青龙偃月刀,跨步、捋髯、怒目,抖动盔帽,满头绒球乱颤:“军校与爷把马带,夺取长沙把功开——”他压低软腭,一股气流从嗓子眼汩汩而出,就像他老家潜河里的水一样,欢快地奔腾着。气流进入鼻腔和颅腔,再回环喷射而出,在练功房里炸开了。四角的蛛网像突然被一阵风掀动了,抖了几下,网中央的蜘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吓得落荒而逃。
红?唉,哪个唱戏的不想红呢?只是不敢想而已,能在这京城顺利搭个戏班,有个吃饭的地方,就很不错了。师父说他只缺一个机会,可机会在哪里呢?机会像天上的浮云,神秘莫测,高不可攀。不走麦城就不错了,关公那样的汉子,临了都挣脱不了一个败局。他程长庚有多大本事呢,是说红就能红的吗?
师父不过是在安慰他而已。
人生就是一个戏台,活着,你就得一直演戏。你不明白自己怎么来到了这个戏台上,又为什么要演戏。你只知道要演下去,不演就无路可走。从一个戏台到另一个戏台,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角色,演着别人的喜怒哀乐。你迷失在了角色里。你是别人,那你自己呢?
大幕闭上,响器息止。也许,你就是那个隐藏在戏台阴影里的人。
晚上程长庚照例喝了一碗粥,吃两只焖炉烧饼。躺下后,他回想着师父说他要红的话,越发觉得不可能。迷迷糊糊中睡着了,醒来后,他又想起了师父的话,再也睡不着,于是披衣出门。才五更天,出了城,寒气逼人,借助天上寥落的星光,他裹紧破大衣,沿着城墙根向西北方向走去。他的肩上还背着个布袋,里面插满了竹笛,都是他亲手制作的,待会练完早课,他还要到集上卖乐器去,挣几个散钱糊口。
一路上,陆陆续续也碰到一些早起练声的同行,程长庚总是低着头疾步走开。按理,天下梨园是一家,同行见了面,打个招呼点个头也在情理之中,但程长庚从不和他们说话,更不会和他们一起练习。到了西直门附近,天仍没有亮,程长庚的身上已经热乎乎的了,皇宫里一辆辆到玉泉山拉水的骡车刚刚出城,再向北走一段路,到了积水潭附近,就人迹罕至了。
所谓遛嗓,旧时指伶人清晨早起,步行至空旷之所或无人之地(以河边或城墙根为佳)遛嗓吊音。一则可以屏气凝神听到自己的回声;二则这些地方空气新鲜,对嗓子有益。遛嗓可一边走一边喊,为的是使嗓音婉转如意,走者为的是气壮。城墙上结了层薄薄的冰,程长庚在墙根前站定了,这里是他每天固定的练习地。他对着那亮晶晶的冰面,开始行腔运气,一口热气从丹田发出,在力量的作用下源源不断地喷出,形成了一股气柱,冲向城墙。程长庚唔、咿、啊地练习一番,由低而高,由高而低,反反复复。气柱喷射之处,薄冰化了,夯土墙上出现了一条明显的水渍。
嘎——程长庚一愣,气柱折了,寒空中的一声鹤唳打断了他的练习。此时天色已亮,程长庚看见空中飞过一只鹤。不错,一只孤零零的鹤。别看它离群了,可鸣声嘹亮,如钹炸响。难怪《诗经》中说“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鹤都是成群结队而行,这只鹤怎么离群了呢?又要到哪里去?这么冷的天,它能不能活下去?程长庚满脑子疑问,肚子却饿得咕噜咕噜地响了。
天光大亮,人越来越多,今晨的练声也就此结束。程长庚开始往回走,依旧是低头疾步,远离人群。自三年前在京城梨园首次登台却败走麦城那天起,他的头好像就没有抬起过。
那是他终生难忘的一天。他的舅舅张坦四处送礼求情,好不容易在大栅栏外的一家戏园子替他谋到了一个登台的机会。他才十三四岁,毕竟还是个孩子,哪里撑得了那等大场面?几百双眼睛都在看着他,一紧张,难免手脚哆嗦声音颤抖,安庆土音一个接一个地蹦了出来,什么把“马上”念为“马山”,把“路旁”唱为“路盘”,把“被窝”念为“被笼”之类。这下好了,砸锅了。有人骂道:“什么玩意,乳臭未干呢,就想当角儿?”还有人骂道:“话还不会说呢,就跑到台上唱戏,这不是欺负咱们是外行吗?”喝倒彩声四起,叫喊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程长庚感觉自己被推到了波峰上,又突然跌进了浪谷里。啪的一声,一只鞋子打在他的头上。他一蒙,还没回过神来,什么花生壳、香蕉皮、脏手巾把子之类嗖嗖地朝台上飞来。京城的观众都是戏虫子,对伶人的要求很高,尤其喜欢轰新人下台,没有点绝活休想在他们面前打马虎眼。舅舅冲上台,一把抱起外甥,狼狈地逃出了戏园。
到了外面,舅舅啪啪地打了自己几个嘴巴子,说:“都怨我,一心想让你早点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没想到弄砸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