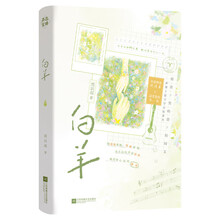《奶茶千杯少》:
生于西湖边,长于富贵家庭,胡培月的世界从来跟江时一不同。
小小的白净女孩儿,是父母的心头肉,母亲燃一撮百步香,盈香满室,培月倚在父亲身旁,读着在他膝盖上摊开的《野天鹅》绘本。耳濡目染,她从小就知道,人要为穿在自己身上的东西负责。八岁跟着母亲在欧洲各国像逛街一样逛博物馆,十岁那年听别人推荐卡其裤,已会发问:“哪种?超窄?slim-fit(修身)?over-size(超大码)?喇叭还是直身?”十二岁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美学价值。
她的眼睛,看不到阴暗潮湿的角落,油漆剥落的墙壁,老鼠飞快窜过的街巷,为几百块医药费发愁的人家。世界是她的游乐场,遍布三件头套装、玫瑰红领带、黑色腕表,意大利白菌、暹罗燕窝、黑海鱼子酱,她心仪俊美的大卫像,倾心精美繁复的糕点,迷醉剧场的光与影。当她念完高二,准备到英国念艺术史跟文学时,身边人毫不意外。他们还预见到,她以后会走“对的路”,嫁给“对的人”。
若干年后,她挽着青年才俊丈夫在同学聚会上现身,大家觉得她不过自证了对本身的预言。
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她青春期即将结束时,也曾经有过短暂的脱轨。
十七岁那年,她拿到大学offer(录取信),到香港找朋友玩。朋友是新移民,住在西环,地铁港岛线尚未延伸到此处。唐楼潮湿,攀爬至朋友家那一层,半层楼的灯是坏的。胡培月天真地诧异,这跟朋友在杭州那个敞亮开阔的家,相差甚远。
附近就是海味干货市场。坐在朋友家窗下聊天,市声像潮声一样涌进来,把咸鱼腥味也灌进来。她捧着杯子,低头喝一口,总疑心杯子里也有腥味。
晚饭后,胡培月乘车回铜锣湾酒店。已是十一点多,沿路所见,崇光三越酒楼食肆外,竟都是行人。她去过的地方不少,但每次都有父母、长辈、老师陪伴在侧。一个人独自出门,还是初次。她临时起意,不去酒店,决定信步走走。逐个橱窗地看,渐至迷路不知归处。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只得拉路人问,开口说普通话,对方面带疑惑地听完,张口讲一串粤语,又给她指引方向。她点头谢过,迷迷糊糊往那个方向走,直至走到一条巷前,十分茫然。
这时巷内有猫叫声,在这人流稀少的地方,听来颇为疹人。接着便是酒瓶子打碎的声响,她赶紧往回走,眼前却不知何时,在两旁已关闸闭店的食肆前,站着两个古惑仔打扮的男人,抽着烟,对她说了句什么。
“什么?”她下意识回话,瞬间后悔。她暴露了自己非本地人的身份。
两个男人对视一眼,其中一个把烟头一丢,踩在脚下,另一个挽起袖子,都向她走来。
这时突然斜着走过来一个年轻男人,直接牵起胡培月的手,用普通话跟她说:“原来你在这里啊。”拉过她就往马路对面方向走。两个男人在后面盯着看。
胡培月任由他牵着自己,两人走到马路中间,男人低声说,不要回头。她嗯了一下。风吹过来,将她头发拂乱。她松开被牵住的手,拨开乱掉的头发,瞥见男人的侧脸,轮廓分明,端正好看。现在他们已经在马路另一头了,男人回头看,见那两个男人已经消失,便松了口气,对她说:“这附近龙蛇混杂的,你小心点。”
胡培月嗯了一声。
她就这样认识了江时一的爸爸。一个年轻人,到香港来投靠亲戚找点事做,其他人叫他海文。但她总觉得他不像是个普通人,因为他送她回酒店的一路上,都有古惑仔模样的人跟他打招呼。她鼓起勇气,把这个疑惑向他发问,他笑起来:“那些不是古惑仔,是财务公司的人。”他没解释自己为什么认识他们。她想,这个世界有很多她不知道的事情。
她在香港又多待了数天,打算在这里过生日。这么跟他说时,他微诧。她那时候年少,不知道跟男人这样说话,等于直通通地告诉对方,我喜欢你。他吸了一口烟,半晌,狠狠点头:“好。十八岁生日,你打算怎么过?”
胡培月想了一圈,说:“我要去澳门,我想看一看赌场。”
他们到码头,等船过澳门,附近传来杨千嬅的《少女的祈祷》:“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般恋爱,再挤迫都不放开。”他们上了船,在没人注意时,第一次接吻。
进了赌场,她看他坐在百家乐赌桌前,面前堆着筹码,他低头,缓慢而专注地将牌揭开,看到牌面的刹那,又轻声失笑,微微摇头,非常迷人。那一瞬间,她突然决定,要把自己像一件礼物一样送出去。
十八岁的第一个月,胡培月回到杭州家里。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爱的男人说:“生下来,我养你们娘俩。”
这种言情小说里的桥段,胡家怎可能让它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尤其对方是来历不明的野男人。在得知手术会有危险后,他们被迫默许女儿将孩子生下来,像打发流浪猫狗一样,把婴孩打发掉。将孩子送到男人广东老家后,转手又准备按原计划将女儿送出国。
胡培月天真而稚嫩地抗争,唯一武器也只是自己的身体。服食过量安眠药醒来后,她看到妈妈瘦得像被抽干水,又听说在她洗胃期间,爸爸犯心脏病一度被送医院。她幡然,自己终归要牺牲一部分家庭。被牺牲的,不是初恋跟女儿,就是爸爸跟妈妈。她选择了后者。被送到英国后,英国人阴天里疏离的礼貌,逐渐替代掉亚热带的潮湿回忆。一年多后,当她开始跟身边男生约会时,也不得不凉薄地承认,当年自己太年轻。她喜欢的,也许只是坐在电单车后飞驰,擦过悬崖边的少女情感。
这种情感,当时再壮烈,多年后的此刻,也只是一抹褪色的残血。男人的模样,她已经印象模糊了,心头时时萦绕的,却是她跟男人曾经有过的骨血。那一滴血不光没褪色,还越发鲜红。
那天她刷手机,在看到有人介绍广东江门美食时,提及御记这家店。这让她想起了十八岁那年,她喜欢过的男人。彼时,她只知道江海文是广东人,不清楚具体在哪儿,但依稀记得他提过,家里开双皮奶店,叫御记。
多年来,她凭借御记二字来找孩子。也不知道是玉记、遇记.还是什么,她都搜寻过。广州深圳,她没少去,也没少留意。听说顺德是双皮奶发源地后,还特地跑过顺德,当时正是农历新年,在广东轰隆隆的舞龙舞狮、敲锣打鼓的街头,她踏着满地红色鞭炮纸屑,一家一家寻过去,又在失落中,独自乘机回沪。
这次,在她联系上江伯时,激动得知,江伯真的是江时一的爷爷,又遗憾获知,海文早在十几年前已车祸丧生。但他俩的孩子还在,在北京念书,逢寒暑假回来。
胡培月这样一朵富贵花,即使落在凡间,也不会开在成年后江时一的视线范围内。虽有血肉连接,然而她们属于不同阶层,即使在同一家商城遇上,也分属不同消费光谱。江时一是一株野蛮生长的小树,小树是不会跟温室里的花朵相遇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