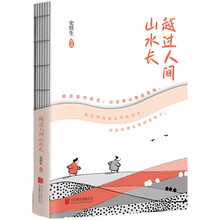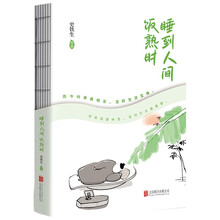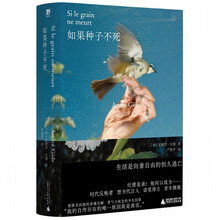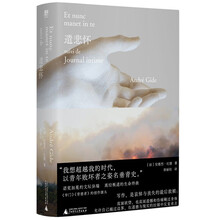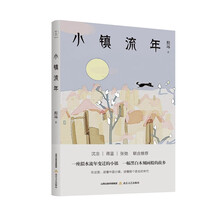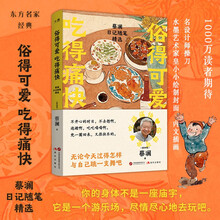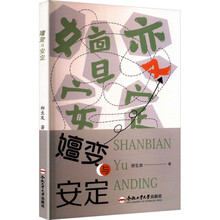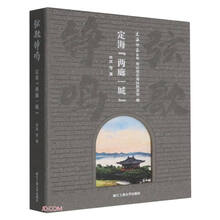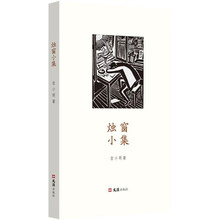《在结束的地方出发/跨度新美文书系》:
毕业的时候,父亲和刚满十八岁的母亲领了结婚证,民族学院的王维舟校长为他们主持了婚礼。那时候母亲已经是共青团员,风风火火的,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父亲默默陪着她,两人背着被卷,搭乘解放牌军车,到了那批毕业生分配中最偏僻的雷波县烂坝子乡和相隔几十里的桂花乡。
在彝族村寨里,母亲住在一个用竹枝和稻草铺垫的废弃碉堡里,四面通风。父亲在周围观察了一圈,找来松木与竹枝把窗户和门扉勉强扎上,才到自己的乡里报到。两个年轻会计各自带着十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彝族同胞,在小凉山的密林里开展基础性的乡村会计、出纳工作。
那个年代运动不断,深山老林还有特务出没。二十岁出头的父亲除了忙碌的财务工作外,休息时间还要拎枪带着民兵进林子抓特务。在乡里,他为人老实,做事踏实,不喜虚张表功。领导不断加码压任务,他也埋头不吭声。可是他工作越努力,越是引起某些乡干部的嫉恨不满,还受上面责备,两头不讨好。母亲劝他对乡里领导报的产量数据不要太较真,有机会也主动向领导反映反映,父亲犟着脾气就是不肯去低头。母亲开始“恨”父亲没出息。父亲心里憋着气,但还是不声不响,埋头做自己的。
到大姐出生后的第三年,母亲终于得到批准,一个人带孩子回重庆探亲。离家八年未返的母亲背着我两岁多的大姐,告别家乡,翻山越岭再回到烂坝子乡的时候,不得已超了几天假。此事被一位领导以母亲“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留恋大城市的花花世界”为由,趁着干部整风运动,上报组织要将母亲精简回去。不可思议的是,素来寡言的父亲听到消息就连夜赶到雷波县政府,去四处申述母亲因超假被错误处理的问题。可在那个年代的阶级斗争面前,个人的前途命运完全无足轻重。母亲最终还是被取消民族干部身份,发回原籍。
更不可思议的是,父亲立刻向组织提出了退职申请。要知道,那时的国家干部主动退职还是比较罕见的。且不说干部身份意味着的个人生活保障和某种象征性的荣誉,在组织尚还需要你存在的时候,作为个人单方面决然退职,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自毁前途的叛逆。更何况父亲这样一个从农村出来、一直寄人篱下的穷小子。
解放前,父亲的父亲被抓壮丁,病死在路上。奶奶靠做手工,养不活家里两个孩子,把五六岁的父亲从老家西充送到重庆,寄养在父亲的二爸家。父亲的二爸,也就是我们的二爷爷家,后来孩子也越来越多,生活维持起来也很是艰难。父亲年龄上是老大,得不停地喂猪干活。对于那段生活,父亲对我只说了一个字:苦。
退职后,父亲抱着大姐,和怀着四个月身孕的母亲回到了重庆。那时候真是一无所有。父亲不答应去南岸比较宽裕的外婆家,而是带着母亲和大姐回到沙坪坝双碑的二爷爷家里,满满一大家子人挤在一起。他每天起早做凉粉、凉面,挑着担子到街上去卖给路过的钢厂工人和家属。据说,父亲和母亲做的凉粉、凉面在团结坝那条街上每天都一销而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