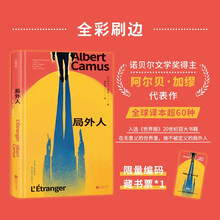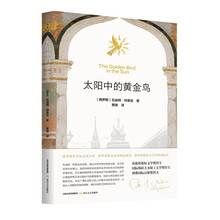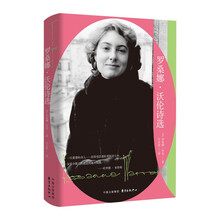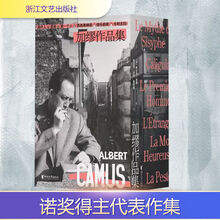一、《错误的喜剧》来源文献[s6]
导言
《错误的喜剧》(The Comedy of Errors)*早在《**对开本》中印行。剧本被划分为几幕及若干场,是莎士比亚篇幅*短的剧作(共1777行)。几乎没有确凿证据支持多佛 威尔逊(Dover Wilson)所提出的“该剧被大幅删节”的观点。第三幕**场中出现的打油诗曾被视为证据,认为该剧是对早期某部作品的改写—或许是1577年由圣保罗男孩剧团(Paul’sBoys)上演的遗失剧作《错误的历史》(TheHistorieofError),又或者是1583年萨塞克斯剧团(Sussex’sMen)所上演的《费拉尔的历史》(AHistory of Ferrar)。但更可能的情况是,正如E.K.钱伯斯(E.K.Chambers)所指出的那样,莎士比亚在本剧中如同在《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和《爱的徒劳》(Love’sLabour’sLost)中一样,“有意识地以拟古的形式作喜剧实验”。本剧的创作时间不详。*早的演出记录是在1594年12月28日,于格雷律师学院(Gray’sInn)上演。但人们在托马斯 纳什(Thomas Nashe)的作品和另一部戏剧《费弗舍姆的阿登》(Arden of Feversham)中,发现了一些与《错误的喜剧》在用语上的相似,提示其成作时间可能更早,或许可追溯至1592年。本剧在主题与风格上也与《驯悍记》相近,可能创作时间略早于后者。
本剧主要取材自普劳图斯(Plautus)的《孪生兄弟》(Menaechmi),同时亦借鉴了其《安菲特律昂》(Amphitruo)。在16世纪,普劳图斯的作品有多个版本,毫无疑问,莎士比亚拉丁语造诣颇深,能阅读其原文。在**对开本第二幕**场的开场舞台提示中,将以弗所(Ephesus)的安提福勒斯(Antipholus)称为“Antipholis Sereptus”,显然是对《孪生兄弟》序幕中(第Ⅰ.38行)“puerum surreptum alterum”(被偷走的那个孩子)和(第41行)“qui subreptusest”(那个被拐走的孩子)的呼应。剧本**幕中,另一位孪生子被称为“Antipholis Erotis”,在第二幕第二场中写作“Errotis”,显然与普劳图斯剧中妓女角色埃罗提乌姆(Erotium)有关,亦可能是“Errans”(迷失者)或“Erraticus”(漂泊者)的印刷误植。直到1595年,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才*次被译为英文,由威廉 华纳(William Warner)完成,其译本于1594年6月10日登记版权后出版。莎士比亚或许曾阅读该剧手稿,当时尚未出版—华纳曾将该译本和其他普劳图斯喜剧译作用于“其私人朋友之娱乐”,据推测这些译稿在朋友间曾广为流传。此外,华纳是一位普通法院的律师,曾创作散文集《牧笛潘神》(Pan his Syrinx or Pipe,1585)及长篇史诗《英格兰的阿尔比恩》(Albion’sEngland,1586),并受到亨利 卡里 亨斯登勋爵(Henry Carey LordHunsdon)的赞助。后者于1586至1596年担任宫务大臣,莎士比亚所属的新剧团即于1594年归其麾下。据记载,该剧团或即为那些在1594年12月28日于格雷律师学院的庆典中,嬉笑中被称为“由一群下贱平庸之人”上演《错误的喜剧》的演员团体。华纳在其译本序言中所称的“许多令人愉悦的错误”,可能启发了莎士比亚为其剧作命名。该标题揭示了剧中主要的喜剧手法,与加斯科因(Gascoigne)在其喜剧《设想记》(Supposes)中使用的“误会”、“伪装”、“欺骗”等主题形成呼应。华纳译本第五幕第73行中“妻子自称为stale”亦可在莎士比亚剧中找到呼应(2.1.101:“poor I am but his stale”我不过是他的旧物而已)。
除此之外,两者在语言上的相似处不多。华纳的译本基本忠实于原作,所有较大改动都明确标示、展现出都铎时期翻译的典范风格,亦可作为莎士比亚更具创造性改编的参照。罗素(Rouse)甚至评论说,华纳那种“轻快的对话”在某些场合胜于普劳图斯原作。然而,《错误的喜剧》必须与普劳图斯原作直接对照,才能理解它在漫长改编传统中的地位。
《孪生兄弟》本身便改编自一部作者不详的古希腊剧作,在文艺复兴时期广为流传,并多次以拉丁文或意大利文上演,亦被作为情节素材加以改写或挪用。例如:红衣主教比比耶纳(Bernardo Bibbiena)的《卡兰德拉》(Calandra,1513)、切齐(G.Cecchi)的《妻子》(LaMoglie,1550)、特里西诺(Trissino)的《极相似者》(I Simillimi,1547)以及菲伦佐拉(Agnolo Firenzuola)的《明眼人》(I Lucidi,1549)。西班牙作家胡安 德 蒂莫内达(Juan de Timoneda)于1559年亦推出了西班牙版本,该剧亦在法语和德语文学中流传甚广。在英格兰,自亨利八世时期以来,普劳图斯便颇受欢迎。斯蒂芬 戈森(Stephen Gosson)曾称早期的英国喜剧“皆带有普劳图斯的气味”。如《瑟赛忒斯》(Thersites,1537)和《好大喜功的罗伊斯特先生》(Ralph Roister Doister,约?1534)深受《吹牛军人》(Miles Gloriosus)影响;而《弄臣杰克》(JackeJuggler,1553)甚至预示了莎士比亚在《错误的喜剧》中使用的情节—即墨丘利伪装成奴隶索西亚的桥段,源自《安菲特律昂》。莎士比亚或许正是在其**部喜剧作品中,追溯了“现代戏剧”的古典源头。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普劳图斯提供的简单故事框架之上,编织出高度复杂的戏剧结构。
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来说,罗马喜剧是一种令人捧腹的艺术形式,它将现实主义与情节和风格上的巧思巧妙结合。在1558年出版于巴塞尔的普劳图斯作品前言《论喜剧诗》(De Carminibus Comicis)中,喜剧被定义为一种用韵文表达的作品,“它是一个完整的诗篇,情节复杂或由人物联系而成,讲述一个虚构的情节,内容、事件和事务皆取材于日常生活,类似于人们的日常经历”。该文还探讨了喜剧从粗糙写实的起源开始的发展,并指出在语言和格律的运用上,它力图接近真实的口语表达。“它选择这些节奏,是因为这些节奏恰当合适,并与人类声音的音响高度契合。我们在修辞中应当包括自然之声所能发出的所有表现。”
拉丁文《孪生兄弟》的序言承诺该剧情节丰富,“以斗或斛为量,而以谷仓计”。莎士比亚的喜剧尝试在情节效果上超越罗马人。他几乎必须这么做,因为《孪生兄弟》仅有1162行,对伊丽莎白时期的通俗舞台而言太短。因此,他在“错误喜剧”这一构想中增加了许多误会情节,还加入了比罗马更具英伦特色的元素。
在拉丁原作中,**幕为日常生活打下坚实基础,揭示了公民墨奈赫穆斯与门客佩尼库卢斯、妻子和埃罗提乌姆的关系。身份混淆从第二幕第二场才开始,在那里,厨子库林德鲁斯遇到了旅行者及其奴隶墨森尼奥。第二幕第三场中,埃罗提乌姆认错了人;第三幕第二、第三场中,佩尼库卢斯与女佣也陷入误会。接着展示了这一切给公民墨奈赫穆斯带来的后果,他依次面对他的妻子(第四幕第二场)、门客(第四幕第二场)和埃罗提乌姆(第四幕第三场)。在第五幕中,旅行者被墨奈赫穆斯的妻子(第五幕**场)与父亲(第五幕第二场)及医生(第五幕第五场)误认为疯子。第五幕第七场中公民与墨森尼奥相遇,接着孪生兄弟相认,谜团逐步解开(第五幕第八场)。整条事件链条精心编排,使旅行者有*多次的尴尬遭遇。他与主要人物共发生七次这样的误会;妻子、父亲和墨森尼奥各两次;佩尼库卢斯、埃罗提乌姆、库林德鲁斯和女佣各一次(据劳斯所述)。公民墨奈赫穆斯虽是误会受害者,但自身从未认错人。
对都铎剧场来说,《孪生兄弟》有其局限性,不仅篇幅短,其主线情节展开也较迟缓,序幕(或为后人伪托之作)显得冗长且节奏松弛。此外,该剧所展现的社会礼仪,包括门客制度、娼妓角色和婚姻女性的讥讽语调,皆显著偏离当时英格兰的文化语境。更为显著的是,该剧中妻子几乎缺席舞台,亦无第二位具戏剧分量的女性角色,此种性别结构的单一性亦可视为剧作构建上的局限。前人改编时已注意到这些问题,例如意大利人贝拉多(Berardo)让妻子出场与丈夫争论;菲伦佐拉在《明眼人》(I Lucidi,1549)中也如此安排,其中卢奇多 托科(Lucido Tolto)大吐苦水,抱怨妻子“我原以为迎来的是个伴侣,却像是请来一个忏悔神父—说错了,是个律师,天天审问我折磨我”。妻子回应说:“我以为嫁来有个家,如今却身陷囹圄,成了奴隶,日日被羞辱与折磨。”
在更自由的改编中,妻子的戏份增加了,角色也更丰富。特里西诺在《极相似者》(1547)中阐明其意图:“讲述平民或下层人物的行为和习性,以笑谈和滑稽词语表现 我在喜剧中尝试效仿阿里斯托芬,即古代喜剧的风格。我借用普劳图斯的欢乐故事,改名换姓,增添人物,部分改变情节顺序,还加入合唱团 并根据古希腊习俗省去序言,将故事交给剧中人开场叙述。”切奇在《嫁妆》(LaDote)中拒绝提供故事梗概,“因为如今人们如此聪明,无须事先解说”,他在《妻子》中将背景设定为现代佛罗伦萨,并声明:“普劳图斯的两位墨奈赫穆斯已成为我们的两位阿方索;请小心别像剧中人一样混淆二人。”这也是通过剧中对白而非序言展开剧情。《妻子》也表现出让普劳图斯情节复杂化的倾向:切奇让剧中出现四位老人,孪生兄弟还有一位失散的妹妹,*终与第三位青年成婚,但她始终未在舞台露面。在一些孪生题材的剧本中,一位兄弟变为女性,这就产生了与《孪生兄弟》风格不同的浪漫纠葛,例如比比耶纳的《卡兰德拉》、雷迪吉诺的《吉卜赛女郎》(La Cingana,1545)及其西班牙版《梅多拉》(Medora)。这类演变已脱离《错误的喜剧》的风格,转向《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在《第十二夜》的一个原型—尼科洛 塞基(Nicolo Secchi)的《骗局》(Gl’Inganni[s8],1549)中,一位父亲安塞尔莫被海盗劫持,十八年后获释,与失散多年的孩子团圆,情节与《错误的喜剧》中的伊勤如出一辙。
为了扩展原剧的情节容量,莎士比亚转而借鉴普劳图斯的另一部喜剧《安菲特律昂》,在这部喜剧中,主人与奴隶的“误入”引发夫妻间的巨大误会。《安菲特律昂》或许是普劳图斯*受欢迎的作品。剧中,朱庇特(Jupiter)冒充安菲特律昂潜入其妻阿尔克墨涅的卧房(Ⅰ.3);墨丘利则伪装成奴隶索西亚,并在剧情初始便拒绝让真正的安菲特律昂入屋,并自称是真正的索西亚。不久,真正的丈夫凯旋,引发阿尔克墨涅的困惑(Ⅱ.2),安菲特律昂则怀疑妻子对他不忠。这一连串误会给观众带来诸多笑料。随着剧情推进,朱庇特再次以安菲特律昂的身份登场(Ⅲ),当真正的安菲特律昂试图返回家中时,又一次被“伪装”成索西亚的墨丘利拒之门外,此时朱庇特正在屋内,情节在此达到高潮(Ⅳ.2)。
莎士比亚将类似的“角色错位”结构转化至其自身文本之中,从而在《错误的喜剧》中制造出角色与观众双向认知的混淆。他进一步将“夫遭门拒、替身赴宴”一情节置于剧情中段(Ⅱ.2;Ⅲ.1),强化了其戏剧效果。他本可更进一步模仿普劳图斯的处理方式,但朱庇特所享有的“被宽恕的通奸”在普通人身上显然难以接受,这也触及了莎士比亚一向敏感的道德底线。莎士比亚同时删去《安菲特律昂》中“公民盗斗篷”的段落,改以角色因妻子的粗暴对待与被拒于门外而选择携带妻子的手镯前往波本廷旅馆拜访“女主人”作为动机(Ⅲ.1.114-121):
既然我自己的家门拒绝招待我,
那我就去敲别人家的门,看他们会不会瞧不起?我。
托马斯 W.鲍德温(Thomas W.Baldwin)曾对莎士比亚融合拉丁喜剧元素的实践进行细致研究,并作出如下总结:“《错误的喜剧》的前两幕改编自
展开